
安娜·斯沃尔诗选
安娜·斯沃尔(Anna Swir,1909—1984),波兰女诗人。出生于华沙一个艺术家家庭。童年在极度贫困中度过。德国占领时期,当过女招待,为地下报刊撰过稿。1944年华沙起义中,担任过起义军护士。后被捕,又死里逃生。
斯沃尔从小就迷恋艺术,尤其是诗歌。早年写过不少具有唯美主义的诗歌。二战后,诗风改变,逐步确立自己的风格,出版了《修筑街垒》、《快乐一如狗的尾巴》、《丰满一如太阳》等诗集。她的诗直接,大胆,简洁,异常的朴实,经济的文字中常常含有巨大的柔情,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旅居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极为欣赏女诗人的才华,亲自将她的许多诗歌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读者,称赞她“能用最少的文字讲述最动人的故事”。
·译 者·
门开着
不,我不想驯服你,
你会失去你的动物魅力。
你的狡黠和恐惧
让我感动,
这些特性适合你那奇异的种类。
你不会离去,
因为门总是开着,
你不会背叛,
因为我从不企求忠诚。
把手给我,
我们将在舞蹈中
穿越发出阵阵笑声的黑暗。
腿和手上
神圣的小铃铛,
一个舞姿,
柔软,恰如古老的阿拉伯字母,
发之歌,
在经典地跳动。
销魂的力量
织成秘密。
但又有点归顺,
像你。
第一首情歌
那爱之夜纯洁
一如古老的乐器
和它周围的空气。
丰富
一如加冕典礼。
它肉感,像劳动中妇女的腹部,
精神,
像一个数字。
它只是生命的一个瞬间,
却想成为来自生命的结论。
通过死亡
它试图领会世界的准则。
那爱之夜
有自己的野心。
惊 奇
这么多年,
我一直望着你,
你几乎失去了形状。
对此,我没有意识。
昨天
我碰巧吻了别人。
只是在那一刻,
我才惊奇地发现
在我眼里
你早已
不再是男人。
正如我需要空气
我将玷污我的肉身,
你曾爱过的肉身。
我需要活着,正如我需要空气。
玷污我的肉身,
我就玷污了你。
你不可能去爱一个被玷污的人。
我将因此得到拯救。
我无法
羡慕你。
任何时刻
都可将我抛弃。
但我无法
抛弃我自己。
她的手
母亲弥留之际,
我握着她的手。
在她死后,我焚毁了
她的手触摸过的一切。
惟有自己的手,
我无法焚毁。
梦见我死去的母亲
昨晚,
我紧紧搂着母亲。
我们舞蹈
在柔软的草皮上。
我的肉身融化了
像雾
在她爱的阳光里。
两个身躯,两片雾,
欣喜中交织在一起,
就像我出生之前。
她和我
在我出生时,
母亲的血
从腿间流出。
我们俩都在受苦,
她的超过我的。
在她死去时,
母亲的血
从腿间流尽。
又一次,我们俩都在受苦,
又一次,她的超过我的。
他已答应
聚会上,
他朝她脸部猛击一掌。
她倒下,
人们抓住他的手,
他摇晃着。
后来,他们双双返回,
手挽着手。
她幸福地笑着。
她怀孕了,而他已答应
娶她。
霍 朗 诗 选
弗拉迪米尔·霍朗(Vladimir Holan,1905—1980),捷克重要诗人。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孕育了里尔克、卡夫卡、哈谢克等杰出作家的城市。当过小职员和编辑。1940年起,离群索居,专事写作,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和政治活动,只与少数挚友保持联系,在隐士般的生活中,留下了《死的胜利》(1930)、《弧线》(1934)、《来吧,石头!》(1937)、《云路》(1945)、《弥留》(1967)等诗集。
读霍朗的诗,有一种感觉:诗人总是在轻声说话,语调柔和,姿态诚恳,有时在同自然、生命和宇宙交谈,有时干脆就是在自言自语,关心的永远是生死、存在、爱情、时间等话题。但他的轻柔的声音又有一种绝对的力量,安静中散发的力量,逼迫读者去思索、去想象。他的诗还带有明显的唯灵论的特征。
·译 者·
相遇在电梯
走进电梯。只有我和她。
彼此望了一眼。这就是全部的全部。
两个生命,一个瞬间,完美,欣喜……
到达五层时,她走了出去,而我继续往上。
我明白,这是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们永远不会再见。
我明白,纵然我把她跟随,踏着她足迹的
也将是个死去的魂灵;
纵然她回到我身旁,带来的
也仅仅是另一世界的气息。
雪
子夜,下起了雪。此刻
厨房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哪怕是无眠者的厨房。
那里温暖,你可以做点吃的,喝点葡萄酒,
还可以透过窗口凝望你的朋友:永恒。
当生命并非一条直线时,
何必还要在乎诞生和死亡仅仅是两个点?
何必还要折磨自己,盯着日历,
探究生死存亡的时刻?
何必还要承认没有足够的钱
来买沙斯奇亚皮鞋?
何必还要吹嘘
你比别人受过更多的苦?
即使这里没有寂静,
雪也会凭空想出。
你独自一人。
省去姿态吧。无需任何表演。
星期天,下雨的时候
星期天,下雨的时候,你独自一人,
向着世界敞开。没有小偷光临,
也没有酒鬼和仇人敲响你的房门。
星期天,下雨的时候,你被遗弃,
没有肉体和拥有肉体的生活,
你都难以想象。
星期天,下雨的时候,你独自一人,
不想同自己聊天。
那一刻,惟有天使知道天上的情形。
那一刻,惟有魔鬼知道地下的状况。
书握在手里。诗即将出笼。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1933—1983)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Nichita Stanescu,1933—1983),出生于罗马尼亚石油名城普洛耶什蒂。从小酷爱音乐。中学时,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1952年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他曾在《文学报》诗歌组担任编辑,结识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诗人,形成了一个具有先锋派色彩的文学群体。他们要求继承二次大战前罗马尼亚抒情诗的优秀传统,主张让罗马尼亚诗歌与世界诗歌同步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尼亚诗歌终于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进入了被评论界称之为“抒情诗爆炸”的发展阶段。斯特内斯库便是诗歌革新运动的主将。
斯特内斯库1960年发表第一本诗集《爱的意义》。之后又先后出版了《情感的形象》(1964)、《时间的权力》(1965)、《绳结与符号》(1982)等16部诗集和两本散文集。发掘自我,表现自我,为思维和感情穿上可触摸的外衣,是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他非常注重意境的提炼,极力倡导诗人用视觉来想象。在他的笔下,科学概念、哲学思想,甚至连枯燥的数字都能插上有形的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任意翱翔。斯特内斯库被公认为罗马尼亚当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
人类颂歌
在树木看来,
太阳是一段取暖用的木头,
人类——澎湃的激情------
他们是参天大树的果实
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游!
在岩石看来,
太阳是一块坠落的石头,
人类正在缓缓地推动------
他们是作用于运动的运动,
你看到的光明来自太阳!
在空气看来,
太阳是充满鸟雀的气体,
翅膀紧挨着翅膀,
人类是稀有的飞禽,
他们扇动体内的翅膀,
在思想更为纯净的空气里
尽情地漂浮和翱翔。
忧伤的恋歌
惟有我的生命有一天会真的
为我死去。
惟有草木懂得土地的滋味。
惟有血液离开心脏后
会真的满怀思恋。
天很高,你很高,
我的忧伤很高。
马死亡的日子正在来临。
车变旧的日子正在来临。
冷雨飘洒,所有女人顶着你的头颅,
穿着你的连衣裙的日子正在来临。
一只白色的大鸟正在来临。
充饥的石头
一头动物走来,
吞食岩石。
一只狂吠的狗走来,
吞食石头。
某种虚无走来,
吞食沙砾。
最后我走来
为了吞食这个回音
——什么回音?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音。
害 怕
只用一击,
我就能将她杀死。
她朝我笑着,
微微笑着。
她朝我的眼睛
抬起她那闪烁的眼睛。
她向我伸出手。
她笑着,微微笑着
甩动黑黑的辫子。
可我,只用一击,
就能将她杀死。
此刻,她开始说出
美妙、天真、诙谐的话语。
她好奇地望着我,
稍稍皱了皱眉头,
然后重又
笑着,微微笑着
明亮的眼睛
望着我的眼睛。
当我凝视她的时候,
只用一击,
我就能将她杀死。
枪
枪由三部分组成:
上部,
中部,
下部。
上部由三部分组成:
上部的上部,
上部的中部,
上部的下部。
中部由三部分组成:
中部的上部,
中部的中部,
中部的下部。
下部由三部分组成:
下部的上部,
下部的中部,
下部的下部。
开火!
音 乐
蓦然他们来到树下。
带着一把吉他
给夜晚留下
一道沉重的、三角形的影子。
随后他们开始歌唱,
乐曲向你伸出
它那冰凉的臂膀。
我望着大地,
望着大地深处
以便在你经过时看到你。
乐曲向你伸出
它那优雅的臂膀,它那冰凉的臂膀。
当它用拥抱,
用通常惟有夜色
会在幽暗中电击般
给予你的拥抱
拥抱你时,我没有察觉。
仿佛捕捞的一堆螃蟹
你用自己
款待了乐曲。
蓦然他们离开树下。
带着一把吉他,
带着从夜晚拔出,从夜晚撕下的
沉重的、三角形的影子。
当我朝你转过脸时,
我只看见一副沙砾擦亮的
骨骼。
哦,我的宝贝,我的至爱,
我的女人,
你来得真好。
我用万分的欣喜吻你的眉弓,你的胸膛,
你那装饰手的精致的骨头,
你那穿越永恒的瞬间的骨骼。
诗
诗是哭泣的眼睛。
是哭泣的肩膀,
哭泣的肩膀的眼睛。
是哭泣的手,
哭泣的手的眼睛。
是哭泣的脚跟,
哭泣的脚跟的眼睛。
哦,你们,我的朋友,
诗不是眼泪,
它是哭泣本身,
非虚构的眼睛的哭泣,
必定会美丽的人
眼中的泪,
必定会幸福的人眼中的泪。
特洛伊木马
我是一匹用来对付自己的特洛伊木马。
我的肩膀占领了我的肩膀,
我的眼睛掠夺了我的眼睛。
我的心跳
淹没了
我的心跳,
我朝天空发出的声音
窒息了
我朝天空发出的声音。
我的生命
由于我的生命
无法存在。
我的爱情用我的爱情之马
驮着我的爱情
在城堡周围溜达。
我用我的刀片刺进我的刀片。
通报我诞生的瞬间
因为通报我诞生的瞬间而失语。
我恼怒自己的恼怒,
我欢乐自己的欢乐。
我希望自己的希望,
我哭泣自己的眼泪。
我存在的时候存在,
我不再存在的时候不再存在。
绳结(之三)
我的眼睛不再用泪水
而是用眼睛哭泣——
我的眼眶不断地生出眼睛——
为了让我平静,如果我能平静的话。
啊,我叫喊,
你们,我的手,
别再用手哭泣!
啊,我叫喊,
我的身躯,别再用身躯哭泣!
啊,我叫喊,
我的生命,你别再用生命哭泣!
我盖住了自己,
但裹尸布下
眼睛、手、身躯、生命
正乱哄哄地来回滚动。
绳结(之五)
仿佛看见山在哭泣,
仿佛在沙漠中读到思想,
仿佛死去但仍在奔跑,
仿佛昨天会在不久来临,
就这样我忧伤地站着,脸色苍白,头上冒烟。
非语词
他递给我一片叶,像只带指头的手。
我递给他一只手,像片带牙齿的叶。
他递给我一根枝条,像条臂膀。
我递给他臂膀,像根枝条。
他的躯干向我倾斜,
像棵苹果树。
我的肩膀向他倾斜,
像副多结的躯干。
我听见他的汁如何加快流动
像血。
他听见我的血如何加快上涨像汁。
我从他身边走过。
他从我身边走过。
我依然是棵孤独的树,
他依然是个
孤独的人。
一种结束
真正的手我并不伸出。
除了语词我不用手触摸任何东西。
不然,
被触摸的树会神奇地缩回体内,
就像蜗牛的触角缩回体内那样,
变成一个句号。
我不去触摸椅子。
不然,它会缩回体内,
变成一个句号。
我不去触摸朋友。
还有太阳,还有星星,还有月亮,
我什么也不能触摸。
尽管我恨句号,可是天哪,
我恰恰居住在句号里。
马林·索雷斯库诗选
马林·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1936—1996)生于罗马尼亚多尔日县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曾就读于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1978年至1990年,任《枝丛》杂志主编。1994年至1995年,任罗马尼亚文化部长。196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孤独的诗人》。之后又出版了《时钟之死》(1966)、《堂吉诃德的青年时代》(1968)、《咳嗽》(1970)、《云》(1975)、《万能的灵魂》(1976)、《利里耶齐公墓》(3卷,1973—1977)等十几部诗集。诗歌外,还写剧本、小说、评论和随笔。他善于以自由的形式,用通俗的语言来叙述某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或某些普通的事情。然而,他的不拘一格的简单叙述不知不觉中就会引出一个深刻的象征。表面上的通俗简单时常隐藏着对重大主题的冷峻思索。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时常包容着内心的种种微妙情感。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都能成为讽喻的题目,因为他认为“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
罗马尼亚评论界公认他为“二次大战后罗马尼亚文坛上最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称赞他“为实现罗马尼亚诗歌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译 者·
远 景
倘若你稍稍离开,
我的爱会像
你我间的空气一样膨胀。
倘若你远远离开,
我会同山、同水、
同隔开我们的城市一起
把你爱恋。
倘若你远远地、远远地离开,
一直走到地平线的尽头,
那么,你的侧影会印上太阳、
月亮和蓝蓝的半片天穹。
圣 火
再给太阳
添些树枝吧,
听说
几十亿年后
它将熄灭。
倘若找不到树枝,
就把有希望变成森林的
平原
以及可能早已变成森林的
山峦、月亮和天空
扔进太阳。
无论如何,
你们得扔些什么,
一些树枝,
一些生命。
瞧,太阳已经开始
在我们脸上闪烁,
将我们的脸化为美与丑,
化为昼与夜,
化为四季和岁月。
眼 睛
我的眼睛不断扩大,
像两个水圈,
已覆盖了我的额头,
已遮住了我的半身,
很快便将大得
同我一样。
甚至比我更大,
远远地超过我:
在它们中间
我只是个小小的黑点。
为了避免孤独,
我要让许多东西
进入眼睛的圈内:
月亮、太阳、森林和大海,
我将同它们一起
继续打量世界。
眉 弓
今天,我遇见一只
爱我的眼睛,
期望我住在
它的眉下。
可是一朵云走来,
眼睛立马关闭,
吓得逃到了
你的脸上,
紧挨着另一只眼睛,
紧挨着并不爱我的
额头和嘴巴。
拉奥孔
儿子抓住父亲的腰,
拼命拉扯,
拉得骨头
都吱吱作响。
父亲抓住胡须
或头颈,
运用几千年的经验,
鼓足力气
拉扯。
惟独祖父
抓不住任何人,
面前只有空气,
没有躯体。
他开始哭泣,
紧紧抱着
怀里的一只圆球。
镜 框
我家的墙上挂满了
镜框,
看到镜框里什么也没有,
朋友们认定
我存心
将他们触怒。
床的上方
还有一块空地,
每次醒来
我总觉得
有人在打量我。
的确,那里
有团球形的光
在不停地跃动闪烁。
可周围没有灯盏,
没有磷粉,
也没有睁开的眼睛。
尽管如此,
床的上方
有人在呼吸,呼吸。
天晓得哪颗星星
正在远方闪烁。
由于物体奇特的
反射原理,
它的灵魂此刻
敲打着我的墙壁。
明天一定得在
这块地方
挂上一个镜框。
伊昂·佛罗拉诗选
伊昂·佛罗拉(Ioan Flora,1950— 2005),生于南斯拉夫。1973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语言文学系。当过中学教师和编辑。曾任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书记。已出版《诗歌卡片》(1977)、《有形世界》(1977)、《劳动疗法》(1981)、《事实状况》(1984)、《死床上的小猫头鹰》(1988)、《记忆杀手》(1989)、《紫色的脚掌》(1990)、《瑞典兔子》(1997)等十几部诗集。罗马尼亚评论界称他为“一位清醒的、有着强烈反诗姿态的诗人”,始终意识到语言的局限,认为诗人仅仅是些书写者。
快乐,反省
我本可伸出手。
本可将你触摸。
本可把你保存。
气息变得愈加重要。
这是生存状况的
一种未曾透露的快乐。
一种纯粹的反省。
此刻没有下雪,天气也不好。
我的眼睛迟钝。
我的目光笔直。
杯子的影象在颤抖
熟苹果强烈的气息。
一天的中间,紧密的联结,
同我称之为土地、自由
和宇宙空间的一切。
眼睛笼罩
山和覆盖山的雪。
事物被删去的轮廓。
我想我或许会被词语咬伤。
松弛的手。
液体的状态。
没有任何理由沉默。
一阵热浪让
杯子的影响颤抖。
书写者
疲惫的人们陆续经过。
或许可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
我勉强察觉出
你的手臂在光中的运动。
物质在迁徙。
或许可以说出许多。
瞧我这个书写者。
瞧我这个城市的编年史撰稿人。
每日三餐
从外面打量的文学。
身体的紧张,装模作样。
每天踩踏的土地。
有人面对面走来,却对你
视而不见。
没有一点暗示指向自然。
指甲。
猎物坚硬的肉。
应该详细描述一下感觉,
描述一下每日三餐。
不是自杀。
不是经济问题。
死亡的结尾
公鸡在鸣唱。也许是夜的开端,
也许是一次攀登,也许是巨人的诞生!
也许是迷失的时刻,刺进我那动脉
纵横的胸膛以及肌肉以及刚刚采来的海绵。
一如以往,我棱住了,眼睛盯着
星光,这是夏天。
我等待着大大小小的国王洗劫我的肝
和书籍。
吁!
吁,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国王!
没有下雨,但野马群将从地里升起。
没有闪电,
没有雷鸣,
但火灾即将爆发,在象牙世界,在胸骨,
在小橡树。
吁!吁!
倘若我往下望去,大地将从根上裂开。
倘若我在流动的水中凝望自己的面容,
我的心弦将更加脆弱,我的脸庞将充满脓肿,
而白色的蠕虫将替代其他的分泌物,
从我的臂膀蹿出。
公鸡在鸣唱:死亡正在结束。

译者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出版过《水的形状》《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孤独与孤独的拥抱》等诗集、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等图书。2012年起,开始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要译著有《我的初恋》《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水的空白:索雷斯库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诗选》《深处的镜子:布拉加诗选》《风吹来星星: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等。2016年出版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曾获得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西部文学奖、捷克扬·马萨里克银质奖章等奖项和奖章。
点击链接可查看:
“未来诗学”专栏往期文章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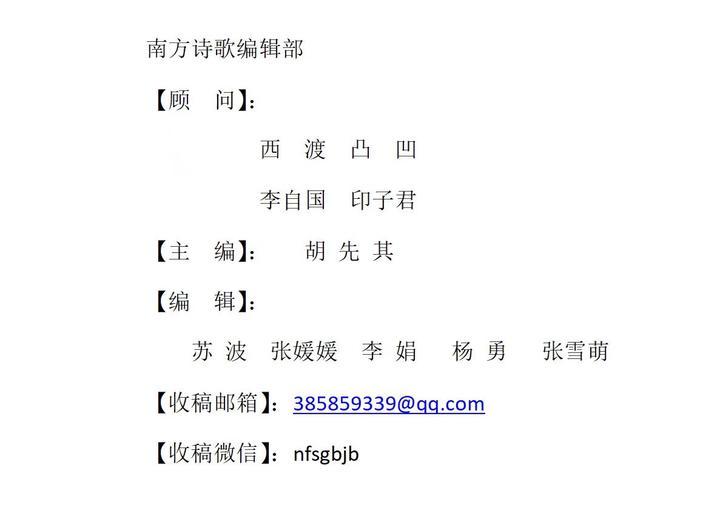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申明:刊头配图如未注明作者,均取自网络公开信息,如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二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三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四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五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八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9月目录
林宇軒:春天的贗品欣欣向榮
“香樟木诗学”:梁小曼|“我想做一只虚空缓慢的龟”——答敬文东
季羽:城市的灯光碎落一地
“他山诗石”:明迪 译【斯洛文尼亚】阿莱西•希德戈20首
同一片海洋
赵汗青:《红楼里的波西米亚》诗选
“未来诗学”:霍俊明|公开的知识与隐秘的缺憾:1990年代诗歌再认识
刘萧:武汉哀歌
“香樟木诗学”:钱文亮|关乎当下与未来的语言风景 ——关于梁小曼的诗
卢文悦:不正规的评论 ——读葭苇诗集《空事情》及外一首
“崖丽娟诗访谈”:李心释|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否定”诗力说
“90℃诗点”:娜夜&张媛媛|以少和慢抵达
彝文前景堪忧?彝族出现大诗人?——明迪访谈彝族诗人
“品鉴”:卢圣虎|在夜航里闪光的诗人——王键诗集《异乡人》读后
陈建:十年(生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