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给Samuel Pollard、Lillian Mary Grandin、李多迦
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
——饶起孝(1840—1911)
你们要进窄门。
——《马太福音》
第一间 堂屋
第二间 庭院
第三间 幽闺
第四间 慕溪楼
第五间 回廊
第六间 书斋
第七间 窄门
第一间 堂屋
爆竹声断。焰硝的清苦还搅着冷空气往屋里钻。
我起身掩门,但见院中雪意
被夜色氲出罕见的幽蓝。
父亲大人酒后略坐,便早早躺下。
守岁者只剩哥哥、启明和我。
煤炉在我面前,烘得手心发干,
套在棉鞋里的脚,却捂出了冷汗。
“启明……”哥哥舌尖的词
绊倒在陡峭的无言里,
衬得窗外风声格外清晰。
我凝神细觑黄铜烛台,火芯仿似老者
一点点往下耷垂的脑袋。
“辛亥年了……”启明终于说,
下一句自然是不会有的。
我已习惯这样的对话,尽管
不只一次想过——它们本该有
轻舟的叙述,张力的转折,更兼
牡丹锦簇的结尾。
沉默扩张,在屋内空无的部分
咬开黑色无底洞。
一道隐秘的伤,再度伏流般漫开,
洇湿心板上回旋的阴纹。
今晚觥筹咣当之际,我几乎已快忘却
它挑起的痛感。
但此刻,它又在我皮下叛乱,肉里扎营。
这狡猾的惯犯,早就精于探索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路径。
哥哥又端起酒盅,启明一口饮尽杯中残余。
白天还明亮如新的堂屋,此时恨不得变成一座坟墓!
而我们,是墓中的活死人吗?
为什么是我们?又为什么,选择了我们?
——想到这里,我双肩一抖,脚更冷了。
我需要一盆热水,一碗巧家红糖姜汁,
一个可靠的被窝与好梦,
绝不是现在这样,绝不是。
“睡吧。”哥哥吩咐我。
我半抬眼皮轻瞥启明,
他仍低着头,双手交叉叩膝。
跨出门槛的瞬间,他的声音才递过来,
像一束迟到的烟花闪烁我身后:
“外边风大,蜡烛会熄;你最好
打上新买的小灯笼。”
第二间 庭院
上月,哥哥从广东回家,
数年不见,身上的旧痕与新潮,
宛如双面画的折扇。
“上次离家,我还蹲下来,捏了你的脸。”
他送我一瓶双妹牌花露水。
从遥远海岸,他带来
美孚灯、照相机、《国风报》,
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同学启明。
第一天,他们打开行李箱,
把衣物挂到院里晾晒。
“一路天阴气湿,好在昭通冬天太阳猛,
不然,人也得发霉。”
第二天,哥哥叫来工人,启明搭手,
弄走了院中假山,卵石,以及那个
有水无鱼的鱼缸。
只留一树腊梅:
“如此,疏朗了。”
第三天,梅树成为他们摆谈的据点。
北方,哈尔滨鼠疫惊魂未定;
南方,水患粮荒,请愿不息。
还有那些只能压低声音谈论的事——
逢人经过,语词便似野兔
一步跳到壮游、渔樵和外国女人的汗毛。
嘁,拙劣的小伎俩!表姐梦莲却很吃这一套。
哥哥回来后,她一天能编出十个理由
路经我们家。近日她
眼睛越眯越小,笑声越扩越大。
“水仙花最好养活”、“天麻粉能护发”,
她反复嚼筋【1】女人才关注的话题。
他们也识趣地嗯啊,点头,延展几句。
没出息,我心想,
男人是另一个物种,永远不可能懂得女人。
“你爱吃酸辣草鱼?这个我最擅长!”
梦莲对哥哥自夸。
真是吹牛不眨眼,只有我清楚,
她从来不进厨房。
明显是怕我冷笑,她急急搂过我的肩:
“我俩个,明天该去慕溪楼了!”
“That’s wonderful!”【2】哥哥附和。
“黎梦莲,可别让我说……”我甩开她的手走向闺房,
感觉到启明眼角余光,
正将一幅寒梅图,画在我后腰上。
注:
【1】昭通方言:啰嗦,计较。此处指啰嗦、话多。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2】太棒了。
第三间 幽闺
我在房中洗浴。
门外,启明的脚步声从回廊那头蹀来,
香柏桶里,水纹如縠皱划开。
倏尔足音远去,我展眼,满屋素霭。
无须求证我也知道:
不只一次,他的目光在我身上画着那幅寒梅图。
当然,以启明的冷傲,定会换个叙述:
他,不过是“碰巧”,让我意识到自身
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
罢了,叙述只是翻花【1】,
占上风落下风,皆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一个人的高傲尚可假冒石头,
两个人的高傲,却是鸡蛋碰鸡蛋。
都会碎的你晓得吗。尽管梦莲说,
“爱,就是放下你自己。”
近日,她把研读《马太福音》的时间,
车【2】来学做酸辣草鱼。
每见哥哥一次,她眼里就多出一抹
不同的味道,
或咸,或甜,
或葱,又或姜。
我只会写诗,不会做鱼,更何况是为
净画枯枝,却不画花的拙劣工匠。
我承认,启明的沉默令我困惑:
有时这些树枝缠绕我,俨然温柔的手臂;
有时挠我,抚摸我,有时又硌疼我;
更多的时候,它们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力量包围我,
无论站,坐,躺,卧,我都像被透明的细线捆着。
我在心里骂人,砸东西,摔门而去,
在他面前,却只能扮演灰面【3】般的lady【4】。
呵,既非他庄重的妻子,亦非他轻快的情人,
怎么可以用命令或撒娇的口吻讲:
“先生,请停止在我身上作画。”
想到这里,我把脚一蹬,
桶底的水花直溅小腹。
噢,今天的水咋这么烫!
我通体的肌肤,浸透出不曾有过的红晕。
真是受够了!我爬出浴桶,
用铁锚牌毛巾擦拭着身体,
突然想起,这块毛巾是启明送的见面礼——
赶紧扑香粉!接下来,我还得
换好干净衣服,翻出首饰盒,
戴上祖父留下的珍珠项链,
手携梅花形捧炉,穿过庭院,
掸开暮色中扬眉飞眼的雪霰,
面若凝玉,和启明坐到一张饭桌前。
注:
【1】昭通方言:翻花绳。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2】昭通方言:挪转,匀出。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3】昭通方言:面粉。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4】淑女。
第四间 慕溪楼
过辕门口,
经陕西庙,妈祖庙,两湖会馆,
一所书院,两座鸦片馆,三家饭店……
每次,我去慕溪楼的路上,
马帮汉子,站街妓女,黄发垂髫,
总有人指点我的大脚。
豪迈一点的,吹个口哨,眼珠骨碌转;
含蓄一点的,站开两步,掩嘴偷哂。
伯格理牧师打着绑腿,背着苗民送的方背篼,
手提药箱,朝敉宁门小跑。
“又有人病了?”我问。
“是,就怕石门坎大雪又封山。
——外面天冷,你快去烤火,
艾玛刚给炉子添了煤。”
在慕溪楼的小客房,牧师夫人艾玛,
为我和梦莲端来热乎乎的下午茶:
“尝尝我做的昭通土豆泥!哦不,
大不列颠老奶洋芋。”【1】
这俩口子坚信,上帝特别恩赐了艾玛
一条黄金舌头。
当年她来昭通不足三月,已能
用一口溜刷的方言,在菜市场讲价:“相应点!”【2】。
“大山包【3】让我想起苏格兰高地。
到了那里我才算开启:
神呼召我离开故乡,必会为我预备另一个故乡。”
艾玛夫人还在赞美大山包洋芋,我却越过她的蓝眼睛,
看到幼时的海。
那年我三岁,祖父决定离开泗水,
回故乡看雪。
为此,他特地哄我:
“我爷爷说,洒渔河能滑冰!
只怕你回去,堆雪娃娃【4】会堆腻。”
……船至西贡码头,祖父从一个戴斗笠的商人手里,
为我买了一串珍珠项链。
我攥紧它,举到眼前,
一条汀滢的乳白,
在海天织就的蓝绸缎下,带给我某种惊异的怅然。
那是我对海最后的印象。
回船上不久,我高烧,病倒,
待记忆的店铺重新开张,
看到的,是昭通济川门前的耍猴人。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5】
珠白与蔚蓝的叠影,在梦莲的背诵声中渐隐。
我忍不住瞟她一眼,正好同她目光交集。
唉,这哪是交集,是稳稳抓住了对方的小秘密。
黎梦莲,你真行,
明知是无果的意马心猿,
明知我也会和你一样承担,还偏要
趁艾玛夫人没注意,朝我乱挤眼。
我的手从苏格兰格的桌布下穿过去,
想狠狠掐梦莲的大腿。而她的记诵声已凌乱: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always… ”
“Always trusts.”艾玛夫人提醒。
“Always trusts, always, always…”
现世报啊黎梦莲,今天注定要卡壳。
她低头,再抬头,看看艾玛夫人,再看看我。
真要命!我们在二次相接的目光中,
看到对方通红的脸。
造孽【6】的梦莲!幸亏被抽查的是她不是我。
“夫人,爱太难了。”我替她说。
注:
【1】老奶洋芋,昭通一道以土豆为原料的菜肴,与土豆泥有相似之处。
【2】昭通方言:便宜点。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3】昭通高山草甸,平均海拔3000多米。
【4】昭通方言:雪人。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5】“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见《新约·哥林多前书》。《林前》13:4-8节,对“爱”有集中阐述。下文梦莲背诵经文亦出自此处,意为“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6】昭通方言:可怜。西南官话常有此表述。
第五间 回廊
倘若这深宅是一座模型,回廊是其中一张
可对折的硬纸,
在两头的我和启明,就能被折进
一条紧密的直线。
不,它应该是一页会飞的糖纸,
是新世纪最鲜馥的如意坐骑。
然而,事实最喜欢打妄念的脸。
多少次,在回廊上相遇,
我们不过微微颔首,侧身礼让。
只有一次,启明停下来,问:
“听说你写诗?”
我迟疑了一下,如实回答:“写。
但写作并没有解救我
心中的爪哇虎。
它从热带来,见过壮丽的大海。
在这苦寒之地,却像是
丧失了曾有的奇力。在
找不到出口的生活里,它
左眼饿出了凶光,右眼生出了荒芜。”
“如果是我,我会感谢它。”
“感谢一头我无法驾驭的猛兽,
且任它把我拖入深渊?”
“不,你有全然的能力喂养它,
享受它与诗激起的奇妙关系。”
“你试过?”
——他再次用画梅枝的目光环视我,
就在我想要愠怒的前一秒,他开口了:
“因为我心中也有被困的猛虎。
它时刻准备着,等待
一场酣畅的狂奔。”
嗨目光,我们心灵最忠实的传感器,
这个新春,它忙前忙后,在回廊飘来递去。
我其实并不在意,我的目光是否也向启明
透露过笨拙的异样。
而梦莲目中清雰点醒我:
她与哥哥,我与启明,
已陷入某种困难的无解关系。
男人们向往伟业,
像纽紧的麻绳,轻视丝线的烦恼。
他们怎知女子的丝线,
能绣出一个辉煌旖旎的新世界!
尖得蹾不稳【1】的黎梦莲小姐,
相比云雾般的爱,
我们更需要一场出逃,一张办公桌,一位Jane Eyre【2】。
走出去,“口”字形的回廊,才不会是
局限我们脚步的迷宫,
而是我们枕风做梦的后花园。
“他不会爱我的,”草鱼厨娘还在倾诉,
“人家有大事要做。
这点小暧昧,只是他们生活中,
一点可酸可辣的调味品。”
“哥哥不是那样的人!”话刚脱口,
我就为自己的心虚暗中揩汗。
“那启明呢?”她反问我。
一枚苦涩的核桃噎住我的辩护。
两位绅士在漏窗外发出礼貌的邀请:
“你们也在这里!要不要一起走走?”
怨女们的回复则一致干脆:
“不。”
直到他们走远,
启明淡青色的衣角在回廊尽头的拱门里消失,
我把视线从象牙黄的腊梅花影移回梦莲这边:
“他啊,他假装没看见我心中的爪哇虎。”
注:
【1】昭通方言,形容人很聪明。
【2】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
第六间 书斋
有时轻淡,似袖手人,踱步山腰;
有时滞涩,满怀心事,进退两难;
有时蜂拥,有时滚动,蓦然抽身,白驹渺然。
——在书斋替父亲研墨时,墙上的丹青,
常向我变幻岚霏的风景。
不,这些不过是我
无处表露的心象。
因为父亲的山水实在是太旧了!
像古老王朝昏聩的睡相,
纵夜半无人,也发不出半丝闷响。
而父亲的生活,只剩下与旧山水比试沉默。
他用哑口取代高谈,任蒙灰的羽衣裹住琴弦。
自打辛丑年哥哥离家,他就
频繁留守书斋,抄永远抄不完的魏碑。
此前两年,祖父落叶归了根
——如他所愿,送葬的队伍前,立着一只纸扎的仙鹤。
那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秋天,
从银杏叶中旋落的细雨,将族人的丧服,
刷出清幽的煤黑。
抬棺上山的路长,每次我仰头往前看,
仙鹤总在炽烈的唢呐声里摆动翅膀。
难道生与死的界限,就是一张薄薄的白纸?
难道再远的出走,最终都要从遥远的海上返回?
几年后,我才被那场葬礼所困惑,
并在越挤越密的黑云中,成为历史的人质。
但哥哥好像并不曾为此所困。
刚回昭通两年,他就想到广州上学,
因父亲反对,未能成行;他便以此为谈判筹码,
为我换来了一对天足。
三年后,他与邻居胡绍增胡傻儿,同去成都求学。
临行前说服父亲,将我送往慕溪楼学英语。
此后,有传言说胡傻儿入了袍哥,
而哥哥跟随洋人,前往天津营生。
我不只一次想过,如果我们还在泗水……
这怨祖父吗?不怨。很多个深夜,
我独自摩挲起珍珠项链,
总感觉有个声音在召唤。
及至前年,哥哥的家信,
才从广东寄来。而他这次回家,
父亲的双鬓已斑白。
当然,他们并未因漫长的分离和误解,
就学会表达热爱。
无论交谈还是饮酒,这对父子都在
一扇空窗的两面。
看不见的墙,用看不见的尺度,
制约着他们铠甲里的柔情和澎湃。
还好有启明,轻松缓和了父亲与哥哥之间
绷紧的弓。
此刻,他手捧天青色梅瓶,新剪梅枝二三,
来与父亲话别。
这是正月十五。明早,两位浪人,又将踏上返粤的归程。
“浮生如此,别多会少”【1】,
雪后霁色照耀长窗,投下冰裂纹的光影;
映得条桌上,好一盆文竹徒然苍碧。
父亲与启明谈诗,欲赠启明《纳兰词》。
当他折进里间找书时,
我终于挑起内心的支摘窗,越过虚设的香几走到启明身后:
“这里大部分书,很快会被遗忘的。”
“是吗?”他不回头。
“是,”我说,“连同这些画。
一代人的旧山水,却是下一代人的苦果。”
短暂的沉默。
就在我以为一切到此结束时,他将手往后一伸抓住了我的手一股突然的春江水淌过我手掌我深吸一口气,心从嘴里跳出来在书斋内敲响早春的大鼓。
我知道他在说,“你好啊,爪哇虎。”
注:
【1】纳兰性德:《水龙吟·再送荪友南还》。
第七间 窄门
离开书斋,已是下午四时。
回廊上,两人并肩蜗步,天色不觉半暗。
“哥哥外出拜别亲戚,还得两三个小时才能打转。”
“梦莲呢?”启明问。
“在厨房,和妈妈准备晚饭。”
“痴心女子!可惜你哥,要辜负这碗好羹汤。”
“负心男子!我可不会为了爱的人下厨房。”
“那你——”他止步:“会为爱去何方?”
庭院虚空,日光沉隐,骤降的蒙晦里我们对视。
“进窄门。”
“请一起。”
我们在旋转的彩虹波轮中撞入闺房。在我关门的刹那他将我堵到墙边。一双炙热的手捧住我冷麻的脸我在教堂圣歌的合唱里闭上眼。“带我走。”好不容易,我把唇从他舌头的缠缭下躲闪开挤出三个字。话刚脱口我觉察到自己放下了高傲我陷入放弃与交付的双重慌张。“不行,”这是他坚决的回答但他接着说,“今后,你可骑上你的爪哇虎,去与我会合。”
“‘今后’是什么?”
“未来中国。”
“将怎样?”
“一片乐土,明亮,自由,充满尊严。”
“那多遥远。”
“或许并不远,如你期待的新的诗篇。
你睁开眼,它就到了。”
我从春霭的滑翔里饧眼,镜中,启明握着我的腰。
“讨厌。”我掐他。
“别掐,”他耳语,“别让这梦醒来。”
我感到自己在一点点变轻。轻掉的先是棉衣接着是马甲然后是双层里袄最后是红绸肚兜。在两座温软的雪山之上启明的指尖爬过我锁骨的一粒粒珍珠它们真美他说。牖窗正在送进最后一缕天光这宇宙暗得太不像话了可我已游回蓝宝石般的大海。启明用吻在梅树的枝头印下花朵让它们开遍我周身。在海和雪的二重奏中他拥抱着一树梅花而我用尽全部的灿烂贴紧他。
直至我们的骨架挂在一起,厮磨着战栗的爱意。而肉身早已消褪于时间的窄门,在梦之外俯瞰百余年后,一个寒冬的大雪——
在趣马门的核酸亭正式关停那天,
隔着牛仔布的阡陌纹,我再次摸到启明裤裆里那发烫的意志。
当窗帘缝吞完稀薄的暮光,我们汇入激愤的人群。
……很快被冲散在街头……
“启明!”我喊。
只有喧声,一壶煮沸的苦水,在烧红的炉上咕嘟。
再喊。喧声震耳,人流汹涌,寻不到他。
我心一紧,一阵莫名的崩裂恍如熟悉的前定狠击我的绝望。
我含泪奔跑。跑过陡街跑过共赴国难碑跑过早已被拆迁的慕溪楼,穿过颓圮的庭院盘曲的回廊,踢开闺房的门。
“你回来啦?”1911年的我坐在梳妆台前,
面对镜子,静候2022年的我。
“启明呢?”她问。
我无言,透过泪帘,但见她颈上珠链,
错落成两条朦胧的幽萤。
在尘埃低舞的灯笼光下,她起身走向我,
递过一块绣着寒梅的白手绢:
“亲爱的你又绕了回来。
看来,这一百多年,
我们的痛苦真的太深了,
而爱,总是不够。”
时间表:
1881年:哥哥出生于印尼泗水。同年,启明出生。
1887年:伯格理(Samuel Pollard)抵达云南昭通。
1891年:黎梦莲出生于昭通。
1893年:我出生于泗水。同年,清廷承认归国华侨地位,下谕“准华侨归国,并严禁唆扰勒索等弊”,华侨返国合法化。祖父闻此消息,着手筹备返国。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祖父计划搁浅。
1896年:我全家从泗水迁回祖籍昭通。
1898年:戊戌变法。哥哥受维新运动鼓舞,欲往广州求学,未成,为我争取了不缠小脚的权利。
1899年:祖父去世。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哥哥与邻居胡绍增前往成都求学,随后失联。
1905年:伯格理首次到达威宁石门坎。
1909年:哥哥从广东寄来家信。
1910年:立宪派《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理。同年,安徽江浙东北大雨成灾;哈尔滨爆发鼠疫;湖北苏北饥民抢粮;请愿、暴动、抗议、刺杀不断。年底,哥哥与启明回昭通过年。
1911年:元宵节后,哥哥与启明返回广州,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6月,胡绍增在四川参加保路运动,9月返回昭通,带回哥哥与启明就义的确切消息;10月,武昌起义。
1912年:清帝退位。黎梦莲第三次拒婚,开始全职侍奉教会。
1915年:石门坎爆发伤寒,伯格理与黎梦莲在看护病人过程中,不幸感染去世。
1976年:启明出生。
1988年:杨碧薇出生于昭通福滇医院,该医院由伯格理于1902年创建。
2022-12-10——2023-1-27 北京、河北定州 初稿
2023-3-10 北京 定稿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出版《下南洋》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五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西班牙、阿拉伯语等发表于海外,并被收入各种国内外选本。获《十月》诗歌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批评家奖、《扬子江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评论奖等。2021年被《钟山》与《扬子江文学评论》评选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
“未来诗学”专栏往期文章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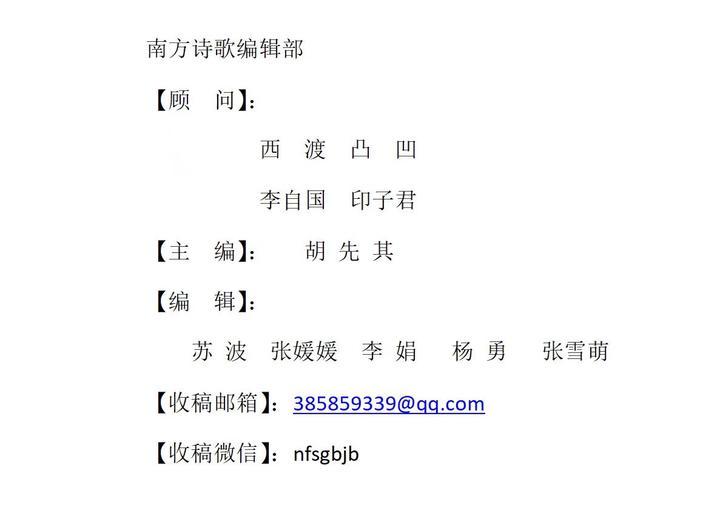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申明:刊头配图如未注明作者,均取自网络公开信息,如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二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三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四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五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8月目录
“他山诗石:程霄扬 译|露易丝·格丽克诗歌新译
“新秦诗”:芸姬|落地的隐喻
“露珠诗社”:白隐|许多镜子路过我们
专辑:在暴雨中呐喊
沈苇:新疆庭院(四首)
“未来诗学”:如何想像一种未来诗学
“新秦诗”:脱脱不花|车厢里
黄立胜:大海潮汐不止
“新秦诗”:李晚|伟大的作品,有令人腰酸的姿势
在暴雨中呐喊
在暴雨中呐喊(续)
在暴雨中呐喊(再续)
在暴雨中呐喊“(续三)
赵野:与阮籍书
“未来诗学”:王东东|民众时代的诗歌与戏剧
“新秦诗”:刘博然|在无序的黑色中
”他山诗石“:明迪 译|杨.瓦格纳20首
赵境:越墙而出
“未来诗学”:西渡|中国诗人的阿基琉斯之踵
蔡建旺:我爱这人世间所有爱的变色龙(组诗)
“品读”:江介|泅渡者洛白:冥思与赋予拯救
翟明磊:呼唤
“90℃诗点:灯灯&张媛媛|因为徒劳,所以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