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掘土
一只土拨鼠在我的地盘挖坑。你的土地
可能也出了问题,朋友我来此,只为做此提醒。
不必开门道谢,你开窗与我对话,想来已经
消解对我当时骗你世界末日来临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我不是谣言家,我也绝望地哭过。那天我回想
前尘往事,什么都想不起。只有万物,纷纷在内心决堤。
它们竟在我的脑中奔逃,这我绝不敢想象。
你还是问我了,土拨鼠怎么出现在你那,又象征什么。
我卖弄我的理解,你别介意。土拨鼠的出现
必然说明我们昔日深埋之物即将出世,这必会引来
一件伤心之事,届时定会地动山摇,生灵涂炭。
哦,你再无下文。你就这么消失在关上门窗之前
的一声“哦”里。我无比惊恐,那只可恶的土拨鼠
究竟会挖出哪件事。大脑保护机制千方百计帮我
解决的麻烦,难道会被这只土拨鼠又咬出蛛丝马迹。
我还不如束手就擒,与其担心受怕。这时你开门了
朋友,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不顾。却见你也面色惊恐
颤抖地说道,你也看见那只土拨鼠了。
我突然想到,我不该来见你。从我的心到你的心
这土拨鼠总需要我来见你一面才能过去。
我们就那么在那里站了一天,在遥远而近在咫尺的
叙旧仪式中,目睹夜色降临。那只土拨鼠不知为何精疲力尽
已经被我们回忆起来的往事深深掩埋。
诱惑
我们伤心欲绝,不是因为
那个早晨,太阳抛锚
阳光退回天空。而是我们共同
打造的房屋在地震中
晃动了一下。它把我们晃动到了
很多年以后我们生命逝去
的那一刻。我们那刻
似乎并不相爱,对视的眼里只有
一种深深歉意。是什么
在日后闯入了我们的生活
并让我们的关系发生巨变。
没有调查的时间,我们就立住了
那在未来晃动的身体。
但我们都察觉到
那由地震带来的裂痕。
我们相拥而泣,发誓更加相爱
我们紧紧盯着那个
将会到达的恶化我们的现场。
一晃多少年过去,它似乎
并不存在。我们犹疑
那场刻苦铭心的分离,许是幻觉。
直到又一场地震来临
用同样的方式
把我们晃回遥远的过去。
那时我们并不相爱
但在人海中碰见,从对方身上
会对未来有一种亲切触感。
待回过神来,我们从过去
也没有察觉到伤害我们
感情的奇怪事物。
它总会出现,很多年之后
我们悔恨地察觉到这一丝期待
正是我们的裂痕之源。
它从那个遥远的幻觉中
这般成长起来,直至摧毁我们
实在匪夷所思。
吹拂
有一次我走到郊外,那里流淌着
一条静静的河。河边一棵粗大的杨柳
我靠在这棵杨柳的脚下,在无数次的恍神中
欣赏远处天空跑步的云朵。
所有日子一样,我那天无事可做
以前的生活回忆起来像一盒过期的
密封糖果。很久以前,我便失去打开盒子的方法
不远处的田地里农夫在梳理苹果
阳光落在苹果树上,也落在人们的脸上
也落在往事的大河里。一切都在铺平地流淌
我的身体里有一个男孩,朝水里
扔着淘汰掉的我。这些年是什么
在暗中决定众我的去留。我感到绝望。
我已经失去最初的样子,只有他保持微笑
常常来看望将他丢弃的我。当我回到家乡
我去田地里面抚摸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草。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我有时会躺在河边听听痒痒的水声
头上杨柳的枝条,绿色的身影
风在水中也将它吹拂,波纹中有着听不清的诉说。
我会看着湛蓝的天空,想起很多走远的往事
我很想挥挥沉重的手,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很多离别,要多年后才起反应。
我常在青天白日看到满天繁星,朝我胸口坠落
我心中有一条高速公路在不停地向
回到我心里的人收费。他们长途跋涉
此刻就靠在我心上,表情温热
那是一条挤满无数落日的河,流动缓慢
在人们的注视中奔赴苍老的大海。
重名
可以看到一双手,曾带着一束花
来到过这片土前。一个人如今
正生活在这堆土里,不知衣食可否忧?
这个人的样子已经整容为一块
竖立的石头。这个人的身体
被建筑得更加坚硬,这个人正褪去
曾经身上柔软的一切。如今
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无法
再撼动他的想法。不知为何
墓碑上,给这个人最后书写的
竟是一个潦草的名字。这个名字里
或许曾有他疯狂的过去。
一些草在他身旁做出防御的姿态
一些花在他身前摇动着美丽的身子
一些风仍在努力吹进他如今密闭的身体
它们都在呼唤他,以鸟语,以花香。
我敢确定这个人肯定是我
远走他乡失,去音讯的某个亲人。
否则我不会在这里停下
难道我们心有灵犀,都喜欢眼前这处静谧
且可以观赏群山的位置。
否则这里距离我的家乡十万八千里
我没有理由突然就止步。
如果只仅仅因为那墓碑上
刻着一个熟悉的名字
我确定那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
他一定是我的亲人
否则我没有理由在遥远的他乡,如此潸然泪下
遥远的从前我们通过电话
那时他说他想消失一段时间。
静音
在对事物重新定义的发布会上
发言者庄严地宣告:我所认识的一切
都大于诸位所认识的一切。
参会者掌声雷动,因这个观点
实在振奋人心。我们对
事物迥异的看法如今似乎得到
最合理纠正。正确的声音由一个人
通通掌握,还有比这
更能快速解决争端的方法吗?
拿着一根火柴,自以为掌握火焰的人
再一次落荒而逃。多年前
这些人曾擦亮自己的眼睛
发表色彩鲜明的言论
却被告知,他们都是和平国度
最邪恶的纵火犯。
现在大家轻松生活,我们明白无误
知道该干什么,如何做
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
我们从发言者那里得到了
最美好的生活图景。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敢想象。我们实现了
最多数人的梦想。为了使
落日更加辉煌,我们需要高喊黑夜
而黑夜短暂,我们每次都会快速度过
这使我们难以置气。
而在无数我们穿过的隧道中
有一个名叫幸福的隧道
只修筑了名字。纵火者曾喧嚣:
我们只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
幸福了一下。这让人们
坚定了他们的判决:罪无可赦。
白鸽在刑场高飞,枪声响起
这是声音的魔术,适合街头表演:
看一种声音如何吹熄
不同的声音。电视上
静音播放着人群欢呼。
没有字幕,不知他们在欢呼什么。
小众
我的嘴巴有点孤独,话最近不来找它。
我的心有点挤,许多事在那维权般闹腾。
我的脑子被抽真空,里面人影不见一个。
我的脚不想走路,最近在等一个筋斗云包裹
只想腾云驾雾,不愿再千里跋涉。
我的菩萨不让烧香,说我最近要求愈加过分。
我的命运手气不好,最近被人赢了几把。
我的伤心下起了雪,飘落在茫茫人海。
我的眼睛时常争斗,左边显微镜里的小我
和右边放大镜里的大我。隔着鼻梁拔河。
我的火气最近有所收敛,消防员们
穿着往事的制服,他们时刻盯着这个现场。
远方
逝去的一物,曾在戈壁滩沉默着走过
有不逝去的沉默吗,在无声世界继续走。
在无人所知的乌尔干车站,知晓你故事的落日
再一次死在山尖。拉住一只求助的手
就是拉住一条冰冷的链子。我们没有管那些
招手的人,他们在后视镜中远去。
盯着我们的苍鹰,还未飞下
就已经在啃食。我们骨头中,还剩多少热血。
只有戈壁滩,只有一个亡命天涯的人
只有雪山,只有一双举起的手。
只有道路旁,淡淡的车辙印
它昭示着来路不明,去向渺茫的一切事物。
这一望无际的苍茫戈壁
多少人停在这,认真地消逝。
这孤独的旅程,只有不停地虚构一个人
陪你说话,才能继续走下去。
一只手接住一只手,自己握住自己
用坚强的手,去握住柔软的手。
你要做的,是作为落日
每天死去,又活来。是一次次把流放地
当做故乡,好生善用。生活不过是
把记住的记住,把忘记的忘记。
群山
那或高或矮的顶点,都站着一个身影
他穿着山林中最为茂盛的一件衣服
用那绿色的眼睛眺望远方,看无数的树木从这里
被运走,成为了建筑的部分
或者成为一场场大火亮哨的一瞬。
这身影所目睹的,便是灰烬。
我曾为没有树木生长的土地默哀
树木不应有有高低贵贱之分
它们都来自泥土,朴实地生长
没有害人之心。我用尽童年整个时光
去认识的树木,在我回到故乡时,
居然全都消失了。更无从探寻的是
那些树上隐蔽的鸟窝。那些飞鸟
也和村里的老人,老树一起消失。
一切都在消失,连同父母
他们似乎也没年轻过,从小到大
都是一副苍老的面容。只有群山
永恒的群山,永远是一张沉着的脸。
它在那里接送黄昏中的孤儿
在那里安抚丧失一切的人们。
夏夜
你见过远山吗
你用故乡的夜色想象它。
那时你用一双工地上回来的手
抚摸着那颗圆圆的落日,它跌进
高耸的建筑中,又偶尔露出半张熟悉的脸。
你总热泪盈眶,说原来是
那么温暖的一只眼睛
在注视着我们身体老去。
说到这,你眼睛里的远山愈发朦胧。
长长的路,回到出租屋
那些相识多年的星星出来
悄悄问,你还在热爱远山吗。
你脸上全是灰,仍认真地点头
你说你仍在奔赴远山的路上。
你仍热爱大江大河依傍的那座巍峨
连绵,深邃,平和。在人世的浪潮中
你随波逐流,没有办法。
吃的很简单,食物于你
只是一个生活不可缺少的步骤。
活着就行,你语气中不含任何
可以让人挑剔的对生活的态度。
去楼顶吹风,那里有几盆月色中的
多肉。它们还在原来的位置
你感到一种彻底的安心。
你还热爱夜空呢,星星高兴地问
它们总有太多问题,要采访
一个无话可说的人。但星星又多么害羞
它们声音细小,努力将身体往前倾
生怕别人听不见自己的话。
这多么像那些,想要说话
却没有声音的人。你伸手
夏天的夜晚,一只萤火虫出现在生活的内部。
那似乎就是星星的脸
它一下钻进你的心里。
哦,这会不会使你的样子
在夜色中清晰几分,包括你的呼吸
似乎都因此,有了一点儿声音。
在辽阔的大地上,一个出租屋的楼顶
你坐井观天。黑色的人生也要怒放
向日葵在远处的田野,你仍记得
某个休息日你看到它们在那里生长。
萤火虫从你手里飞走,它说要去
给更多的人抓住。
这使你想起刚才的落日
它给你的感触,和之前的落日略微不同。
你的身体弯下去,你的手有些无力地垂着
一点一点,你闭上眼睛。
你记起在回来路上,你无意放走的一只
认命的蝴蝶。它困在一只你经常路过
的蜘蛛的网里。不知为何
这只蝴蝶没和今天的落日一起离开蛛网。
它们本都是蛛网的过客。
你怎么解救它的,星星问
它们永远在追问毫无意义的问题。
它们真的关心这只蝴蝶?
你起身离开,打算换个睡处
当扒开那些蛛丝马迹
远山又多么令人窒息。
访山
好像没人再提故乡之山
这是好事。原来怀旧会过时
提过去会变成一件落伍的事。
我的父母,一辈子没走出蛮枝山
以后他们将会葬在那里。
一座山,承载了无数的生命
早已冤魂缠身。泥土的乡亲
死了也在保护着山。
每一次离开我们都会抓走一把泥土
带去异乡。坐着高铁或大巴
他们终于离开了蛮枝山。
很多次,兴奋的他们
不停地说着一路风光。
很多次,他们在梦中隐晦地提出
想要返乡。回到蛮枝山
返回棺中,那里有他们的床。
我曾以为他们在山中痛苦
没想到那里是他们唯一安宁之地。
想到那个盛开着野花的地方
我好像忘了是什么使我生长。
我低下头,奇怪眼泪
躲在眼睛的哪个地方。
我突然记起那个使我哭泣的山岗
许多晚霞款款而来
山之歌谣在回荡,人们在山中
开演唱会。父母并不是不懂音乐
他们用镰刀弹奏着锄头。
我的乡亲们,他们拥有旺盛的生机
讨论着明日。生我养我的乡村
从来就没有衰老。同样的
没有人愿意走出蛮枝山。
许多从小生在在此的
年轻人,没有被山神眷顾
他们不知道山中景色。他们迷失在
访山的途中。很多年后他们会明白
他们追寻的陡峭而崎岖的一生
就是记忆中父母脚下
那座平平无奇的山的一面峭壁。

彭然,男,1996年生,云南昭通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教师。有作品见于《草堂》、《星星》、《边疆文学》、《滇池》、《诗歌月刊》、《江南诗》等刊物。曾获樱花诗赛奖,野草文学奖,淬剑诗歌奖主奖,草堂青年诗人奖。出版诗集《在白马庄》。
“未来诗学”专栏往期文章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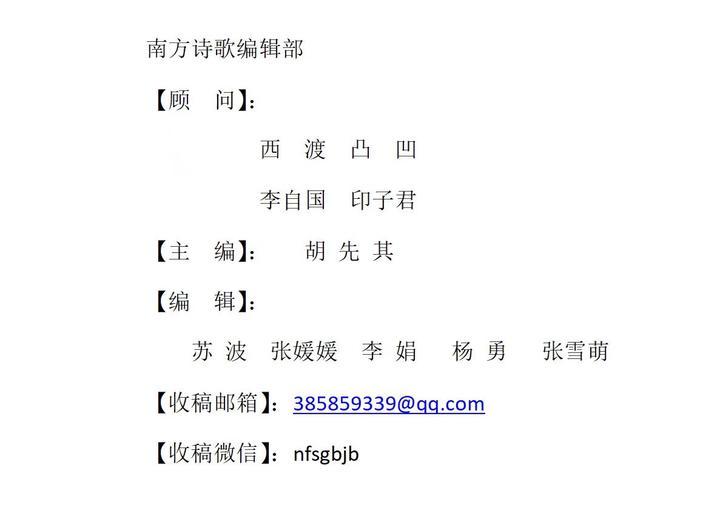
申明:刊头配图如未注明作者,均取自网络公开信息,如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南方诗歌》2021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2年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二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三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四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五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总目录
《南方诗歌》2023年8月目录
“他山诗石:程霄扬 译|露易丝·格丽克诗歌新译
“新秦诗”:芸姬|落地的隐喻
“露珠诗社”:白隐|许多镜子路过我们
专辑:在暴雨中呐喊
沈苇:新疆庭院(四首)
“未来诗学”:如何想像一种未来诗学
“新秦诗”:脱脱不花|车厢里
黄立胜:大海潮汐不止
“新秦诗”:李晚|伟大的作品,有令人腰酸的姿势
在暴雨中呐喊
在暴雨中呐喊(续)
在暴雨中呐喊(再续)
赵野:与阮籍书
“未来诗学”:王东东|民众时代的诗歌与戏剧
“新秦诗”:刘博然|在无序的黑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