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茶馆
李耀曦
泉城济南人,吃自来水过日子的历史并不长。昔日茶水灶遍布济南大街小巷街头巷尾。茶水灶不仅卖开水也兼送泉水到家入户。当年人们一日三餐、饮水喝茶,都离不开这被称为茶馆的茶水灶。但凡老济南人都有一番到家门口附近的茶馆打开水回家冲茶的难忘经历。

早年家住南关永胜街,街口上有座朱家茶馆。
永胜街是一条东西小巷,位于三合街南段路西。朱家茶馆坐落在永胜街东口路南。朱家为街口路南头一家,小院门牌是永胜街2号。朱家把院门东侧两间小北屋作为灶房,里面盘了大炉灶“老虎灶”,在临街后墙上掏开一个落地式窗洞,外面砌了齐腰高的水泥台子,上面铺块青石板,用以放置水壶暖水瓶之类,开了这家茶馆。
我家所住小四合院位于永胜街东头路北,门牌永胜街3号,与朱家茶馆隔街相望,距离不过几步之遥。上三合街小学那会儿,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需沏茶待客,便常遵父母之命,提个竹编外壳暖水瓶,去朱家茶馆打开水。故而对这座街头茶馆,可谓十分熟悉。
朱家茶馆位置很好。虽说是开在永胜街上,其实是处在一个三街口。茶馆门头在永胜街,茶馆东墙外为三合街,茶馆南邻为岳王庙——当时庙已不庙,早已断了香火,只剩下两间破旧殿堂(岳王庙又名精忠庙,民初《续修历城县志》中有关于此庙的记载)。而旧殿堂门马路对面就是精忠街。生意经上谓之“金三角”,故而附近几条街上的居民都到朱家茶馆来打开水。茶馆生意甚是兴隆。
济南人所谓茶馆,其实是茶水灶,既无茶也无座,就卖白开水。此外往往也兼卖凉水——泉水,送货上门。那时济南南关一带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备有一口大水缸。那年月平民百姓都很穷,除冬天在屋内点炉子取暖之外,平日煮米造饭蒸干粮就是在院子里烧大锅底。一般都不会单为烧壶开水而另起炉灶费柴费炭。
济南虽非茶叶产地,老百姓却素有饮茶之风。昔日居家过日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茶。再穷再没钱,也不能缺了那二两茶叶钱。纵然面徒四壁,也不能没有一把好茶壶。喝茶不仅是个人嗜好,更是待客之道,关乎礼数和脸面。此事可谓大矣哉。这也为穷街陋巷中茶馆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民风基础和文化土壤。
朱家茶馆日常经营,主要由朱家老两口操持。说是老两口,是由吾辈小毛孩子看来,其实他们并没多老,当时尚在壮年。朱掌柜“朱大爷”主外,管着烧开水后提壶灌水、照应;“朱大娘”主内,管着在灶旁拉风箱、查看火候、适时向灶膛内添煤。由于常年烟熏火燎,夫妇俩都是灰尘满身、脸孔黝黑,难辨庐山真面目。
各行有各行的门道和诀窍。开茶馆也不例外。拉风箱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也有个轻重缓急,张弛有度,不是一味使蛮劲。刚加入生水时,是慢慢悠悠地一推一拉;待烧到八九成时,速度明显加快,犹如京戏锣鼓点急急令,“咕达、咕达,咕达达”猛拉几把,炉膛里火苗顿时窜起,很快就把灶台上的壶水“拱”开了。而提壶灌水同样也有讲究。有街坊来打开水,朱掌柜立即笑脸相迎,热情打招呼,赶紧从灶台上把烧水壶提过来。但并不直接就往暖瓶里灌,而是提起壶来先朝青石板上点两点,只听“噗”的一声,石板上腾起一团白色蒸汽。据说这名堂叫弃壶嘴儿,美称为“凤凰三点头”。其目的,一是把壶嘴口上方有灰的不洁之水倒掉,二是表明这壶水是刚烧开的沸水。来打开水的若是位家庭主妇,看到这“凤凰三点头”,听到这“噗”的一声,也就放了心。因为济南人都爱喝茉莉花茶,而花茶需用滚烫的开水才能沏开。否则的话,就会说,朱掌柜,请再烧烧,或者说,换一把热的吧。
朱家茶馆的烧水壶最初是铜锡壶,即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阿庆嫂唱词中“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所唱的那种铜壶,由铜锡合金浇铸而成。由于铜锡壶笨重,而且一旦壶干容易烧化,逐渐被淘汰。最后都换成被称为“洋铁壶”的轻便耐用的镀锌马口铁皮壶。
朱家茶馆卖开水,既可现钱交易,也能赊账,还实行包月优惠。记得每逢月初,朱家都挨家挨户向街坊们兜售竹片水牌。人们到茶馆打开水时,便很少带现钱,灌完壶后,随手掏出一根水牌,往青石板上一撂。青石板台边有个小圆筒,朱掌柜就捡起水牌朝圆筒里一扔。如果是带零钱往往也不找,就从圆筒里拿出几根水牌给你。
每日晚饭前后,是朱家茶馆最为繁忙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前来打开水的人络绎不绝,有时甚至要排队等候。青石板砖砌台子上,摆满了由济南保温瓶厂生产的各色暖壶。其中以竹皮编制外壳居多,也有用济南自行车链条厂的边角废料焊制成的,如果是搪瓷喷绘铁皮外壳,那多半是结婚时亲朋好友赠送的礼品。
而所谓“街谈巷议”多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街坊们聚在一起不免拉拉呱扯点闲篇。尤其是那些徐娘半老的女街坊,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大老爷们挣钱多,谁家的小媳妇长得俊,谁家的大小子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听说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以及谁谁家北园乡下的亲戚来了,背来一麻包地瓜,还有半袋子小米,他家这月日子好过了,不用提前去三合街粮店借粮了。话匣子打开,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谈个尽兴。于是这朱家茶馆门前,就成为附近街坊邻居们的“信息交流传播中心”。当年街道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很多情报也大都得于这消息最灵通之处。
开茶馆这营生十分辛苦。早年在济南操此业以为生计者,多是近郊进城打工的农民。朱掌柜正是如此。他原籍济南近郊长清朱家庄,20郎当岁时进城打工,落脚南关。因无一技之长,最初就是下苦力做水夫,从南门泉子里拉来泉水,推着独轮小车沿街叫卖。后来觉得终非长久之计,便学了门手艺,做了糊棚匠,承揽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各种裱糊业务,给有丧事的人家扎天棚,给办喜事的人家装饰洞房裱糊顶棚。年龄大了后,不愿再东奔西跑,遂拿出历年积蓄,盘下永胜街路南2号小院,开了这家街头茶馆。从乡下把老婆孩子接来,作为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之中,朱家茶馆有一段最为兴旺昌盛的时候。那就是济南“三合街药市会”期间。济南曾为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河北祁州、河南禹州、安徽亳州、山东齐州)。药市会原为药庙会,最初是趵突泉前街,那里原来有座药王庙。民国时,药庙会迁移至山水沟街,老舍散文《药集》中曾写到当时的情景。
此时的三合街药市会,已没有多少药材,而是各种土产杂货,但规模很大,依然十分热闹。药市会农历三月二十开市,为期十天至半个月。当时西起山水沟街、南卷门巷、国兴街、三合街,东至祭坛巷,北至正觉寺街,南到圩子外,周围一二十条街上都有货摊商贩。南圩子外空场子上,山水沟黎明坝至南卷门巷口,则扎有大大小小的席棚布篷。马戏团、杂技团(记得大横幅上写“吴绍良杂技团”)、说唱团,还有交通大队的宣传台,每天从早到晚都在那里演出。其间还夹杂着各种小吃摊的吆喝声。
药市会期间,每天三合街上都人头攒动,有时甚至挤得水泄不通。于是位于三街口的朱家茶馆,便在茶馆门前,摆上个小方桌,旁边有几个矮凳马扎子。小方桌上一把大茶壶,几只粗瓷茶碗,抓把粗枝大叶的茶叶,放到大茶壶内冲开,供过往行人和摆摊小贩们饮用解渴。平时干一天,不过挣个两块多钱,这时干一天,能挣到四五块,甚至五六块钱。日进斗金谈不到,翻个两三倍没问题。
济南三合街药市会举办最后一期,是1965年。这也是朱家茶馆最后的辉煌。“文革”开始后,街头巷尾的茶馆不复存在。除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外,街头自来水站的设立,锌铁皮煤球炉子的问世以及煤炭凭票购买的供应紧张,也是茶馆趋于消亡的重要原因。
如今本人早已搬离了老街旧巷,但仍然保持着早晨起来便冲泡上一壶热茶的习惯。端起茶杯品茗饮茶,不由想起当年的朱家茶馆,这茶水品起来遂也有了点岁月沧桑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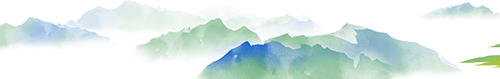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