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词名篇鉴赏(二十六)| 孙光宪《渔歌子》二首
其 一
草芊芊,波漾漾。湖边草色连波涨。沿蓼岸,泊枫汀,天际玉轮初上。
扣舷歌,联极望。桨声伊轧知何向。黄鹄叫,白鸥眠。谁似侬家疎旷。
《花间集》里,还有八首吟咏江湖渔乐的隐逸题材词作,它们是和凝的《渔父》“白芷汀寒立鹭鸶”,顾夐的《渔歌子》“晓风清”,孙光宪的《渔歌子》“草芊芊”、“泛流萤”,李珣的《渔歌子》“楚山青”、“荻花秋”、“柳垂丝”、“九疑山”。李珣的《南乡子》“云带雨”一首,也可视同隐逸词。孙光宪的两首《渔歌子》,写江湖月夜泛舟之乐,表达词人遗落世务、潇洒出尘之想,闲适疏旷,论者叹赏其“竟夺了张志和、张季鹰坐位,忒觉狠些”(汤显祖评《花间集》卷四)。
先看他的《渔歌子》其一。词咏本调,写渔隐之乐。上片描写黄昏月夜的湖景,起二句“草芊芊,波漾漾”,先用两组叠词状写湖边草色和湖面波光,“芊芊”形容岸草丰茂,“漾漾”形容湖水摇荡。在分写岸草、湖水之后,接以“湖边草色连波涨”,双承起二句,把岸草与湖水合在一起描写,湖边芊芊的草色,连着湖上漾漾的波光。“涨”字用得好,湖水“涨”好理解,草色“涨”似乎不好理解。仔细体会,这个“涨”字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单说水势随着潮汐涌涨;二是说湖草临水,无干旱之虞,水分特别充足,长势分外茂盛,看上去竟如随着水势向上涌涨一般;三是说湖上水草,许多就是长在水中或水面,当湖水涨起的时候,水草也随着波浪浮起来。一字之下,是以实际的观察为基础的,所以才显得准确,才有表现力。前三句的湖光草色是一个大背景,“沿蓼岸,泊枫汀”二句开始聚焦人物,交待行踪,渔父泊舟的长着蓼花和枫树的岸汀,这些地点切合渔父的特定身份,具有不可移易性。前结“一轮皓月初上”,境界阔大,当渔父结束一天的捕捞,泊舟岸汀之际,一轮皓月正从天际升起,湖光水月,顿时一片空明。
下片抒写渔父怡然自乐之情。“扣舷歌,联极望”二句,包含着渔父的心理变化过程。泊舟的渔父本来是准备上岸归去的,当他看到湖上升明月的壮美景色,情绪便激动起来。月夜水湄,渔父时而扣舷啸歌,时而放眼远望。“桨声伊轧知何向”一句,是说如此美好的湖光月色,让渔父感觉啸歌眺望仍不能尽兴,于是情不自禁地摇起船桨,荡舟湖上,纵情赏玩这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水月美景。“知何向”三字,见出渔父信舟而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湖光月色,无非美景,娱目赏心,是处皆可,这种无目的而合目的的状态,正是审美陶醉的美妙境界。“黄鹄叫,白鸥眠”二句,以动静的相衬,进一步点缀湖上月夜的恬静。一结“谁似侬家疎旷”,词情迫发出的问句,点醒题旨,渔父快然自足之情溢于言表。
此词溢出了《花间》情词的题材范围,清旷之意,野逸之气,令人神往。词中所写渔父,具有高度的自然审美素养,能够不顾水上生涯一天捕捞的身体疲劳,陶醉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愉悦之中,这样的渔父,在现实的层面也许是不存在的。那么显然,词中的渔父,就是词人的主体人格的镜像投射,是寄托士大夫文人隐逸理想的意象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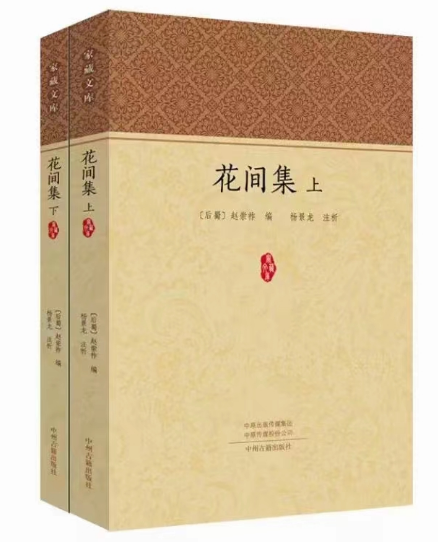
其 二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
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
这首《渔歌子》其二,与前一首一样,题咏本调。上片描写湖上夜景。起二句“泛流萤,明又灭”,先写湖边萤火点点,到处飘飞,忽明忽灭,烘托出一种幽静的环境气氛。接以“夜凉水冷东湾阔”,以肤觉感受暗示深秋的时间,交代泛舟的具体地点,是在宽阔的东湾水面。这里的“东湾”,当指霅水注入太湖的水湾。“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三句,从感觉写湖风的浩荡,从听觉写渔笛的清越,从视觉写万顷湖波,空明澄澈。“金波”本是形容月光的,构词兼顾了月光如水和月色微黄这两个特点。在这里则指月光照耀下的东湾一带的南太湖水面。把上片串起来讲,写的是渔父秋夜泛舟东湾,夜凉水冷,流萤明灭,迎着浩荡的长风,吹奏清越的渔笛,但见万顷金波滉漾,一片水月空明。“万顷”句承接“东湾阔”,是“阔”字的具体落实,展示月夜太湖的空阔浩大境界。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词句“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所写境界,与之相似。
下片描写夜晚行舟,抒发渔隐之乐。“杜若洲,香郁烈”二句,在上片写过秋夜太湖的流萤、渔笛、月光、水波诸多美景之后,再写洲渚之上杜若散发出来的浓烈香气,芬芳了南太湖这个美好的夜晚。杜若是出现在《楚辞》里的香草名,屈原《九歌·湘君》有句“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当是词句所本。这里的杜若洲,就比前一首里的“蓼岸枫汀”的单纯景物,多了一些比兴寄托的意味。在这月夜的湖波上,在这杜若的香气里,渔父的内心受到更深的触动,不免要“思美人”了。“一声宿雁霜时节”,是一种互为主客的双向的蓦然惊觉,渔父的棹歌渔笛惊觉了夜宿的芦雁,宿雁的一声鸣叫惊觉了“杜若洲”旁“有所思”的渔父。南归的大雁和夜晚的霜露,说明时令已是深秋,这一句回应了上片的“夜凉水冷”。月夜江湖的自然美景,令渔父陶醉,他索性荡起双桨,“经霅水,过松江”,聆听着栖宿江湖的嘹唳雁声,呼吸着江风吹送的杜若香气,欣赏着江湖秋夜的清幽风景,享受着那份俗世难得的自在快乐,心旷神怡,乐哉漪欤!“尽属侬家日月”,是审美交感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临皋闲题》),渔父便是个遗落世务、身心舒放的“闲者”,他感觉这整个的江湖,整夜的风月,全都归他所有了。这是一种摆去拘束、回归自然的大自在、大快活、大潇洒。
此词写江湖月夜泛舟的隐逸之乐,表达词人遗落世务、潇洒出尘之想,闲适疏旷,论者叹赏其“竟夺了张志和、张季鹰坐位,忒觉狠些”(汤显祖评《花间集》卷四),不为无因。《渔歌子》或《渔父词》的近源,是唐人张志和首用这个题调的初度创作,《尊前集》所收张志和五首《渔歌子》(又称《渔父词》),表现的就是霅水、太湖一带的自然风光和渔隐之乐,孙光宪的《渔歌子》显然接受了张志和的影响。《渔歌子》和《渔父词》的远源,则是《楚辞·渔父》,其中那位濯缨濯足清浊在我、开解屈原和光同尘的江湖“渔父”,才是后世一切渔隐题材写作者的精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