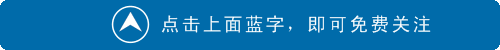
童 年 琐 忆
文/杜浩荡
一日,与发小们闲谈,提到了我们的童年,那时的事情就一下子同泄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下。

1 上学
上世纪的1965年秋天,我们走进了村小学。这所小学是我们两个自然村的村办小学,老师只有一位,共四个年级。这是一所用爷庙改造的小学。这位老师很勤劳,算公办老师。他懂园艺,将学校绿化的像园林。校门口有一条甬道,两边栽着梧桐和木本花,像路两边的哨兵。校门口“八”字墙上分别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组大字。门楼的造型很别致,又高又大,上面站着三只活灵活现的鸽子,曾经有位猎人还对着鸽子开了一枪,见鸽子并没有飞走,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假的。

走进校门,正对面是一个花园,只有月季、刺玫,构成一个正方形。花园中央修了一个圆形的鱼池,里面养着金鱼。鱼池上面是葡萄架,秋天串串葡萄吊下来,给花园增加了无限生机。 花园正北,叫北殿,是二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东殿是一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教室正面的檐墙上都安着玻璃窗,门上也镶着玻璃,靠后院的墙上则是正方形的木框窗,冬季要用纸糊。还有一个西殿没有学生,是老师的柴棚。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式班小学。四个年级才53名学生。西殿、东殿、北殿都用墙相连,把整个寺庙分成两部分。教室和花园成为前院,北殿和东殿相连的地方安了两扇门,从这门进去,就是寺庙的后院,后院很大,足有3亩地,一亩麦田,另一亩是苗圃和葡萄园。园内有一口井,由三、四年级学生轮流用辘轳绞水,来浇灌葡萄树和苗圃。现在想来,很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这就是我开始上学的小学。
报名那天,本村的七八名适龄儿童,由一位大人领着,去见老师。老师姓王,个子高,身材魁梧,前脑门有点秃,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我们当时只觉得他穿得很阔气。他书教得好,在我们两村人的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只要他开口的事,家长们都是有求必应。他用自己的能力把学校美化得很好,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
报名开始了,每个孩子只要能从一数到二十,就算报上了名,然后问父亲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几岁,几月生的,用笔记下来就好了。其实他一看孩子的相貌,就知道是谁家的,因为他和我们那两个村的人都很熟。
第二天,来校交上一元五角钱,算是学费和书本费。每人发了两本书,一本算术,一本语文。算术定价2角8分,语文定价3角1分。还发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语文书开头是汉语拼音,后头是识字,大多是看图识字,字上面标着拼音,很好学的。课文共44课,时隔48年,我仍记忆犹新。第38课是《大雁》,课文只有几句话,“秋天,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我们这个一年级共有12名学生,6张桌子就坐下了,和三年级坐在一个教室。早上,先上早读,然后就上一节算术课。先从1.2.3学起,老师先给一年级上课,上完后,不下课,再给三年级上课。上完课,第一节课就算上完,下课。给一年级上课时,二、三、四年级都在写字。第二节课时,老师先给三年级上课,一、二、四年级写字,三年级的课上完,不下课,接着老师再到二、四年级教室给四年级上课。早上四个年级都上的是算术。 下午用同样的方式上语文。小学当时就只开着两门课。 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就放秋假。秋收大忙季节,学生是要帮助生产队秋收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帮助生产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说拾棉花、扳包谷、掐谷穗等。农村的孩子,都会劳动。
一转眼就到了冬天,天气太冷了,我们的小手,都冻僵了,握不了铅笔,老师就叫一年级学生坐到自己的房子上课,因为我们最小。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是享受不了这个待遇的。因为两个村子,冬季只有老师的房子搭着火炉,要让农民家搭火炉那简直就是奢望。
一个学期即将结束,老师就自己出题考试,自己阅卷。那时不搞统考什么的。
放寒假,已到了寒冬腊月,北风刺骨,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能躲在家里啊,还得到麦地里挑草、挖荠菜,得喂猪啊。要么就得到田间地埂或者崖畔去挖柴,如枣刺根、茅草根等来烧炕、烧锅。手冻裂了,得忍着,好一点的家庭,家里还有点凡士林,抹在裂口上,日子过得艰难的家庭,连这个也没有。
生活天天如此。
2 狼患
那时候,不知道是生态环境好还是发展慢,狼太多了,这个村刚将其赶跑,一会那个村又在赶,喊声震天。
四婆的屋在我屋的东边,是个边庄子,靠窑跟前的墙低,狼半夜从窑跟前跳上矮墙,再从矮墙跳入猪圈,把个半大子猪咬死,吃了一半,又从矮墙逃走。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来,我妈就喊;“狼昨晚钻到你四婆屋里去了,把猪咬死了!”我赶快起来跑到四婆屋里,屋里很多大人,议论着,查看着狼的“脚”印,说着狼是咋进来的,又是咋出去的。我四婆哭的很伤心,猪是她一手喂大的,还指望卖了猪买粮呢!我婆和好几个老人安慰着她。
有一天早上,一老汉在沟南磨地,两只狼来了,他慌忙就上了柿子树,向村里大喊。牛是不怕狼的,牛用角来抵狼,所以狼是不敢进攻牛的。村里人拿着镢头锨赶来了,把狼才吓跑了。
1966年的春天,麦子返青了,生产队饲养室那几头牛最瘦,饲养员就将它们的缰绳一解,这几头牛就恢复了自由,在麦地里随便吃,这叫吃青。
一天大中午,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庄西麦地里有几头牛在吃青,我们五六个娃,就来到庄西麦地里挑草,在麦垄里找寻得全神贯注,我们挑着,忽然听到有人喊“狼”,回头一看,两只狼就从我们身边跑过,后面的大人追赶者,扔石头砸着。我大伯喊着:“狼跑到盖盖儿顶去了!狼跑到盖盖儿顶去了!”那是给在盖盖顶劳动的人打招呼让他们注意防范。狼跑得很慌忙,这两只狼白天藏在半截沟里,被大人劳动时发现的,它们白天没有归山。这是我最近距离看到狼的一次。要不是大人们追赶,我们还以为是狗。常听大人们说,狼是铁头铜沟子,黄瓜嘴,豆腐腰,麻杆腿,扫帚尾巴。今天看见了它们的尾巴是下垂的,嘴并不像黄瓜,和狗没多大区别。

麦子渐渐长高了,可以藏住狼了,我们上学更害怕。
白天,在村旁打麦场畔,谁家的羊拴在那里,狼来吃羊了。羊吓得使出毕生的力气,拽断了羊绳,跑回了家,家人拿着锄头,才把狼赶走。
我大伯说,他有一回傍晚从山上亲戚家拉了一只绵羊回家,在山路上遇见了一只狼,离狼只有两丈远 ,狼蹲在路上,他只好也坐下来,拿出旱烟袋抽烟,羊被吓的回身哆嗦,往人身后藏。狼不走,他抽烟,僵持了三四袋烟功夫。狼怕火,始终没有进攻,最后走了,他才拉着羊回了家。
夜里时常就有人家的猪被狼咬死在家里,或者被狼背走。天明了主人哭爹喊娘啊,家里的零用钱就指望那头猪呀,这可怎么办呀?
麦子抽穗了,家有学生的大人就商议,每天早上由一位家长负责把学生送到学校跟前。
端午前,天气渐渐热了,天刚黑,月亮才亮起来时,邻村人在涝池岸的大皂角树下闲聊,由于有大人在,孩子就在家门口玩耍。谁知狼就从塄上面冲了下来,咬住了一个女孩的腿,拖着往塄上面跑,女孩疼得惨叫。大人就撵,喊着:“赶紧撵,贵贱不敢叫狼换口!”狼开始下口时,由于慌乱是不选择部位的,它换口时,就要咬住袭击对象喉咙,这一口下去,往往使袭击对象毙命,所以不敢叫狼换口。大家把女孩从狼口里夺了回来。从此,天一黑各家就把门关严了!
夏天到了,蚊子虼蚤多了起来,晚上被蚊子咬醒好几回。那时也买不起蚊帐和蚊香,屋里蚊子多时,女人们就点一把火,给火上盖一把麦糠,沤烟驱蚊,本来屋里就热, 这一点,就更热了。
男人们晚上把被子一披,睡到打麦场里去了。因为场里刮着悠悠风,没有蚊子也凉快。我也拿着被子铺上碾过的麦草睡到了一绺,但我害怕半夜狼会来,就睡到了大人中间。我学儿叔说,睡到中间也没用,狼抽蒜薹哩!他这是吓我呢,我心里也忐忑,但看见其他娃有的还睡在边上,我也就不害怕了。

场活毕了,麦草都弄成了垛,苫蔽成丘。场里没啥可铺,男人们也都睡回去了,孩子们当然也就不敢睡在场里了,因为怕狼。
天还热。我三爷就不怕狼,他每天晚上收工后,在家吃个馍,喝点水,把被子一披,天还没黑严,就睡到村口的碾盘上。饲养室的后门正对着碾子。我问:“三爷,你咋睡到这儿?”三爷说:“这儿好啊,石头炕么,又没有个虼蚤。”我又问:“你就不怕半夜狼来了?”“狼来了,给他个腿!我老了怕啥呢!”我也是常听老年人说,狼嫌我老,咬不下!
有一天夜里,狼真的来了,狼先用舌头舔他的脸,他试来脸上冰冰的,急忙坐起,一看是狼,拿起木枕就砸,抽出碾杠就打,同时大喊,饲养员也来了,把狼吓跑了。他接着在碾盘子上可睡。直到天冷了,我三爷才睡回去了。
各家都养着羊,我们这一群孩子经常跟着大人放羊,就常遇见狼,羊遇见了狼,跑得比兔子还快。
山上的大水沟村,有一群羊,由两个壮年人放着,时常受到狼的袭击。羊在山坡上吃草,狼突然从草丛里冲出,叼起一只小羊就跑。山上沟壑纵横,狼很快就摆脱了人的追赶。晚上羊进了圈,圈门上了锁,放羊的人在羊圈旁的小窑睡觉值守。刚睡下,就传来阴森的狼嚎,放羊人起来,响上几个二轮子大炮,听不见狼嚎了,就回窑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放羊,羊出圈时一数,少了一只,查看现场,发现了羊血滴了几丈远。
上下不到两个月,一群羊就让狼糟践得所剩无几了。
狼多为患,狼多为灾,大队干部把这事报告给晏寨公社,公社派武装干事组织了武装民兵荷枪实弹上山,为民除害,打死了几只,狼患才有所缓解。
狼,从此在我的记忆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作者介绍:杜浩荡,1959年生,1980年至今从事语文教学工作近40年。1993年临潼县教育局组织编写乡土教材《巍巍骊山》撰稿人之一。闲暇时写点生活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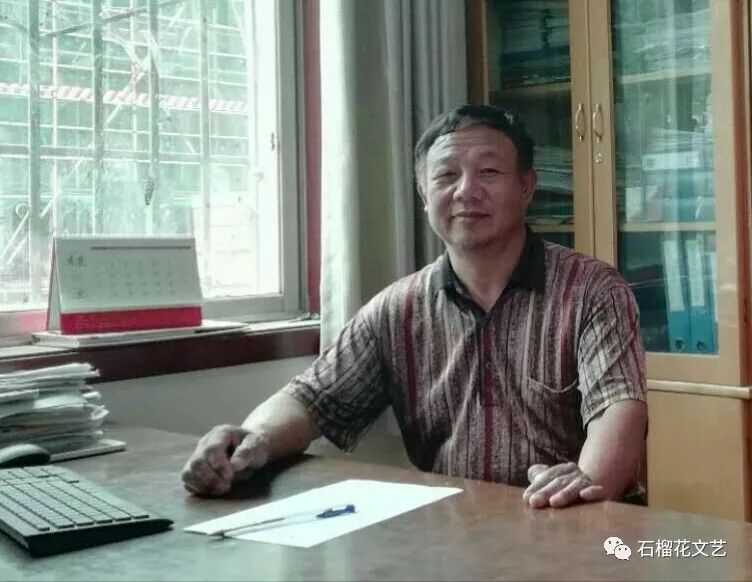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