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文竹(安徽)
你是万有者,万有引力,领受神恩的汪泽
我使用放大的手,像一个侵略者
私心万里的空头君王,攻城略地,据为己有
然后与一棵草商议 “什么可以不朽”
最后才发现:抓住的是自己
忽然有一天,我将星空当作人生的清样
高远的灿烂忙于校对着生活的地形图
只是,这一片星空永远不会打印出来
每一次我只是添加了一点妄想的余墨
感谢上帝,容忍了我对命运的挤压
才漏出了那么一丁点的晶莹色
听到半夜大街上的一阵怒吼,撕裂星空
他立马打开高层的窗户,将这怒吼小心收集起来
将成千恶狮、猛虎、鬼怪关进笼子
失眠之路:剑门关上办起了加工厂
独木桥与啄木鸟同时歌唱
梦幻的起重机撞上洪钟,他加倍
以红日兑换婴儿的伟力,撑一把天使伞
中了魔法的现实展开了一条旷世的生产线
狮虎鬼怪们散发成细密的针线,春雨般穿引
大地上尽是镰刀闪闪的低吟。神的鼻息
像瞬间的花开花合。怒吼的种子全部脱胎换骨

梦境中奔跑的一匹马到哪里去寻找呢
不可能。不可能再塑造出那样的湖泊和草原
梦境中啼哭的巨婴在月下的哪一户人家呢
千家万户中,一位开门的老人承认了自己
梦境中金甲和子弹变幻八十一种活法
大海和天空叠床,魔鬼与天使在梦中安眠
梦境中一直踩在琴弦上的那一双脚
在现实中不知往哪儿放
以后,遇到梦境就将她活埋吧
神赐的土壤,用银河系的水慢慢浇灌
等到春天,会长出奇异的花,树,星空,童话城
可是结果萌出的是另一个梦境
更多的梦境:没有一个目击者
我如何掇拾这遍地的赞美:落叶的言辞
变成了金色的,贴着大地继续发表
几场战争的记载:深层的
白骨与惊悚。恶的礼帽,终于与时间和解
此刻,开往村庄的拖拉机。红茶花。萱草。一只长颈的黄嘴鸟
接着填补这灰暗的缝隙
黑云还在捕杀人间的儿童游戏
我使用天使的蓝刀,掇拾这遍地的赞美
我与被反对的事物连结一体
有些像春风,吹拂着时间的加冕
有些像春风的种子,推翻时间的加冕
前因后果。反对与反对的泥土起伏如画
我没有必要添上一笔,而惯于复原命运
一个完整的时代必有缝隙的部分,豢养出
一只驰骋于孤寂之夜的马匹

胀着。捂着。敛着。藏着
甚至埋下地雷也阻止去踩
一双神明的手啊
却在使用世界
词已变老。而她长出的足
正给大地设色
但,就是一直不愿揭开
像反向的真理
半夜敲门的魔鬼
却是歪打正着
长河落日。市井人生。夜间梦游
——隐藏我与上帝的论争:谁欠了谁的
又是谁,傲慢如暴君?无风起浪
清晨出远门,妻子反复叮嘱
“还有什么东西别忘了装进去”
这琐碎的生活,何时变得完整
像田纳西的坛子置于山顶
这样一个小小的宇宙,却撒下无数的零配件
这组装的无尽的悲喜,冰火一体
风来的时候,往往有两种可能
现代性杀气:摧枯拉朽的闪电战
拖着古典的腿脚,细微、无声
以至于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魏二伯指给我看:他的肩膀上的伤痕
分明是风的狂妄杰作
其实,一阵风是大神的叹息
(一定经历了长久的观察、思虑)
对世界的态度,或是否
改变了世界,你无法分辨、描述
风也赶不上命运变换盛装的速度
多少旧人变新人的传奇
多少中立,预言,倾向性,生与死的戏法呵
哲人爱说:“杀气”易于成为杀机
杀机成生机。这似乎
与爱与仇恨无关,而是指事物的演进过程
而我只是一个劲地喜欢寻找答案
伴随着对于县志里的一个词半信半疑
转而看那东头湾水库的水面被吹皱
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像问题无穷无尽
岸边悬铃木纷纷落叶的果决中
我看到紧要关头的肯定,或否定

八百里的河水托起两岸稻花香
唯有樟树维持着自己的消化系统
站立到底,不会死于非命
群山翻身,我翻身,仿佛一声鸟鸣的
指引与操守,无奈千秋关一带
一则小道消息撕开了世界的缝隙
萌动的熹微加紧脚注,但抵不过
噪音的拖拉机开在南山道上的笔力
灌木丛里,一只虚构的老虎正在吃强扭的瓜
旭日的大手笔在人间惜墨如金
不像舞台上的泪水,成为殉道者的瀑布
如何守住野枣果的青涩呢
安徽与浙江,撕下了各自的面罩
此刻在我的身体里双峰对峙
孔夫子在岸上曰 “逝者如斯夫”
二千年的人间一下子被淹没
仿佛梦幻的加急版,水波涌动
落日忙于给虚白的灵魂涂抹色彩
此刻的宛溪河畔,两个人在争吵
抬头四望,被流水撕开的大地
什么也没有发生,像一个人
变成两个人,与宇宙的内力对抗
看那飘荡的乌篷船,悠闲,顶着的
一个典故在河流的胃里无法消化
而站在河边的两个人,其实是
一个人与另一个早年的自己

言不由衷的部分统统变成了野外的菜花
我就不想滋养天下了
一幅胜景可以充当虚无的调味品
美与功利也会隐藏各自的雷霆
当然,这样的副产品对于我来说
是危险的。神恩论在某种程度上
适合于我,比如不经意间的伤口
与境界说有了某种分界线
只是,也有一致的琴弦
需要谁来拨响呢?不可说
向内转吧,而悲欢只是一对
长了触角的可有可无的副词
仅对一个人有用,无关乎真理
我一直领会绵羊的眼神,花蕾的心底,和风的温柔
当魔爪伸向白雪的宫殿
识春的小蜜蜂忙于暗渡陈仓
庭院深深深几许,归来的镖队
埋葬了刀斧。重续书生小姐的情缘
那一年,末世论流行
门前的狮子仍在加紧上演世纪的骗局
但我还是流连于围绕着狮子的绵羊,花蕾,和风
只是回首一惊
看那一个狮子一样的人的现实版——
满口利牙,满脸皱纹、横肉、杀气
站在路口是一位凶煞
挂在墻上是一把悬剑
随时会不翼而飞,落入人间
啊,上帝!能否
剥下他的一层或几层皮
取出那一张年幼的稚气的俊美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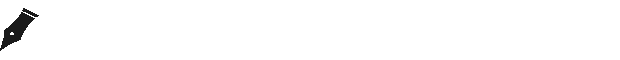

方文竹,60后写作和批评者,安徽怀宁人。80年代起步校园诗歌。早先与友人创办先锋民刊《门》,后组建滴撒诗歌群体并主编民刊《滴撒诗歌》。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散文集《我需要痛》、长篇小说《黑影》、多学科论集《自由游戏的时代》等个人各类著作21部。1997年6月11日中直三家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方文竹作品暨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研讨会”。入选《中国新诗三百首》《新诗百年诗抄》《中国文学年鉴》等。倡导“抵抗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