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当是始于忧患,终于启蒙
——张中海《黄河传》阅读随笔
宋遂良
30年前走黄河的“楔子”
《黄河传》是一本大书。我这里说的不仅是它体量大,六七百页,也不仅是说题材内容。母亲河横亘天地山海之间,比我们炎黄子孙的先人出现还早十万年、百万年,无论怎么写也书之不穷,歌之不竭。但书的体量大不代表它就大,关键是它有无充足的内含和外延。它不只是为黄河立传,而且是为我们先辈写史,为我们历尽沧桑的民族、不屈不挠的炎黄子孙竖碑,为我们这些后人曾经的愚昧蛮干而痛心疾首,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而呼号。
我还在泰安一中教书时,张中海从滕县七中放麦假回去收责任田里的麦子,路过泰安,借去看孔孚先生的机会,顺便去了我泰安一中一趟。我并不写诗歌评论,但我已经注意到中海的诗。1983年他一组《泥土的诗》诗在上海《萌芽》刊发,是写农村责任制实现后,一代农民在连雨天焦躁不安“晴天也烦,雨天也烦”。我觉得他是准确“扑捉住了一种时代情绪”,就给他写了一信鼓励,又嘱咐他严格把握分寸。这组诗后来获了《萌芽》奖。1985年他民办教师转正后,我通过同样搞文学理论研究的淄博师专教务长于清才,介绍他前去任教,淄博师专领导痛快地答应了。可就在他去师专跟领导见面后出来回家的火车站上,他遇见去东营孤岛支援油田建设的运兵车,就拐了个斜子,乘运兵车去了油田(此经历他在诗集《混迹与自白》有记录)。由此开始了他和黄河三角洲、黄河的不解之缘。多少年过后的今天看,那次出行,可以视作30年后他不顾一切走黄河采风收集写作素材的一个“楔子”。
文学当是始于于忧患,终于启蒙

(山师大文学院三剑客。中、左为宋遂良教授、吕家乡教授,时年90岁;右为袁忠岳教授,87岁。)
2016年前后,张中海在采风结束后的写作间隙中,有时和我们山师大袁忠岳、我、吕家乡几位老者喝酒聊天。听到他说他积郁多年的思考,说被采访对象如胜利油田老指挥李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大江大河从来都是万寿无疆的”感慨,港口专家候国本关于“恢复王景治河原则,重现中华民族光辉”一类言论,我就推荐给他一首谭维维和老艺人合唱的华阴老腔:
为什么天空没了蓝色?
为什么大地没了绿色?
为什么我们已经知道结果?
为什么我们还在挥霍?
我想,这一定是中海需要的。也果然在出版社2022年4月版本590页里出现,遗憾的是终稿里没有了。原因我们当然明白,部分删除从来都是必须、必要的。现在看绿水青山,天蓝云白,但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华阴老腔所用嘶哑的喉咙所喊的,毕竟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事实。就像今天我们看着黄河改善了治理方略后,黄河已经二十年没再断流。但整个国人,绝不仅仅是黄河口的人,都曾经对黄河断流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不然,就没有后来163位院士联名呼吁拯救黄河,没有《黄河保护法》出台。而最初唤起张中海创作冲动的,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愈演愈烈的黄河断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社会发展不是从来这样?所以,文学作品的魅力从来就是源自忧患,终于启蒙。它忧患意识所创造的社会进步,也在《黄河传》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的三十年间不断得到验证。30年后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的决策与态度,也使源自忧患意识的《黄河传》创作,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正面案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将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人物描写贵在刻画出人物灵魂
“我们属于这片国土以前,她已属于我们。
她成为我们国土,比我们是她的人民,更早 一百万年!”
我知道这是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写给他西部国土名为《彻底奉献》的诗,原意是“她成为我们国土,比我们是她的人民,更早一百年”。张中海把“一百年”私译为“一百万年”,并且把它用作题记,一下子赋予了弗洛斯特的这首诗以更具份量的内含。是的,和黄河所创造的华北平原相比,它西部国土一百年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一本河传涉黄河母亲河的前世今生,它所表达的主题也不是单一的。我这里仅以书尾第十五章《长河夕烟》、十六章《新大陆》谈一下张中海由黄河断流所引发的有关水土保持及河流伦理方面的思考。
《长河夕烟》是写水土的。水土是人类万物据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切谷宝生产本源,”“众生依蔽,诸草出地,无量有利”。黄河来水减少,黄河泥沙增多,是因为自汉代以来人类的过度开发。为了让一个大而美的大西北建成,新时期以来,国家投入巨大资金,退耕还林种种政策配套,当地政府和老乡,也有自发的行动。我注意到张中海写了几个治沙的民间英雄,事迹都很感人,都是传统上的“歌德”。作者在这里给我的启示是,歌德写正面人物关键是刻画出人物的灵魂。我只举占篇幅很小的殷玉珍一个例子:“家住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农妇殷玉珍治沙知名度远在牛玉琴、石光银、张应龙之后,谈到她为什么舍命治沙,她说,她嫁到沙漠边缘这个小屋后,整整四十天没见一个人影。一天,她远远看到一个人好像要从屋前走过,就撵上前想搭个话,可过去时,人已经走远。就立马回家拿了个脸盆,把这个人的脚印扣住,每天都过去看看…”(见554页)。
“每天都过去看看…”,人物灵魂就活灵活现了。
在这种正面讴歌里,充满了对现代人、当然也包括秦人、汉人破坏自然、破坏生态愚蠢行为的反思。再举一个例子,在第十六章《我的黄河口》一节,中海在写黄河口灯会龙灯舞中“卧龙迎祥”以象征“取水”的民俗后,他的幻觉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看见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上的饕餮,从关锁十重的博物馆展厅逃逸而出。滚着履带,张牙舞爪,扑向眼前的一切——千万年前的青山、远古流来的绿水、斑斑锈迹的帝都,包括新起的村居,包括先人长眠的墓园,推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人们四散而逃或拍手称快。转眼之间,刚出土不久的饕餮又掉进自己刚掘出的坑里。”(见610页)
人并非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他不是宇宙中心,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也并非进化的终点。人什么时候把河及万物视为与自己同等的生命,与它共存共荣,河流才有希望,人类也才有希望。翻遍全书,特别是有着归纳作用的后两章中,此类闪着思想光辉和语言魅力的文字比比皆是。所幸如饕餮一样疯狂的年代已经远去,国人痛定思痛,已经对自己曾经的贪婪有所反思并诉诸行动。以作者后记叙述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例,在他开始写河传的1990年代,他还是一个激进的“经济至上主义者”,到他20多年后再重新开始书写时,他已蜕变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曾经的“驯服黄河”的橫匾,在内蒙三盛公引黄水利枢纽也已被收进博物馆(169页);原来荒芜的大西北,以延安周围为例,也已变得一片葱茏;颓败的黄河口,重新变为鸟与鱼的天堂。黄河也从上世纪愈演愈烈的断流,变为20年不断流。这一切,都不是轻易到来的。我们所要追溯的,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悲悯,所以才有世界眼光
“若是没有野兔、布谷和白鹳,一个田野还叫什么田野?土生土长的精灵与大自然穿着同一色彩的衣裳,按一年四季的节拍作息、作乐、作爱,与土地形成最亲密的联盟。它们不是禽兽,而是和我人子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革命,它们总是永存——不能让一只兔子活蹦乱跳,不能让一只翠鸟一个猛子扎进水中衘出一条鱼的田野,它一定是贫瘠的”。(597页)。
仁和,宽容,悲悯。张爱玲说,因为懂的,所以慈悲。我说,因为悲悯,所以才具世界眼光。同样看一件事,站位不同,所看到的场景绝对是不一样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疯狂的拥护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至上主义者”,再到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再到年满花甲后的人道主义者(见作者后记),就像作者笔下的黄河,经历了上游峡谷激越、中游的曲折奔袭,河到下游,就宽缓不迫了。人生阅历和不断的反思、忏悔,终于使中海变得宽阔,所以行文才悲悯。类似的文字还有不少,再如:
“母亲河养育了我们,我们今天给她一点反哺,我们能失去什么?”这是中海描写一群专家在风雨夜里去看长江时所做的反问,又何尝不是他在河边的夜里依偎母亲河雕像此时此刻的心思?细雨菲菲的夜里,他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即便看不清,看不到她白日里雄风浩荡,但仍能感觉到她在她儿女——我们人类身边的喘息。一个活生生生命的喘息。河流孕育了我们,孕育了我们的文明,我们今天给她以反哺,我们能失去什么?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条河?整个世界!”
这不是张中海河传主题的全部所在,但,仅仅是这些,我也仍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有着世界眼光的一本大书。我这样说并不是刻意拔高,他所写一个乡下农人,也具这个高度的。《长河夕烟》一章“保卫黄河:一组吴起的绿化照片被认为是假的”一节,中海所写米脂县高西沟村坚持七十年不辍的水土保持,其做法是不跟风开山辟田,始终实行种草、种树、种粮“三三制”,其效果是“高西沟的泥沙,没一粒进三门峡水库”!外人问起当年的带头人,当时已经84岁的老支书高祖玉说:“人除了想着自己,还得有个全人类的思想…”
“全人类的思想“?这当然属于大话了。可由这个地道的农人、老人之口说出,又是多么实在!作者这样感慨。我们有人可能已经看到过联合国最新策划拍摄的广告片:一条灭绝七千年的恐龙,摇摇摆摆地登上了联合国讲坛,它要敬告人类的话我们一想便知,那就是“人类不要把自己整没了”。而这个思想,张中海早已在内蒙章《鄂尔多斯兴亡》“庞然大物,曾经的恐龙王国”一节中,形象地予以表达。地质队员发掘恐龙坟场,12具未成年的恐龙偎依蜷曲在一起。曾经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今何在?它又是怎么消逝的?没有答案。只有他所引用做本章题记的美国奔驰公司总裁办公室所挂的条幅:在这个世界上,如恐龙一样消失的庞然大物比比皆是!
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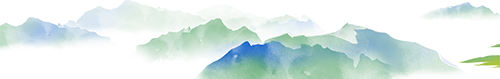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