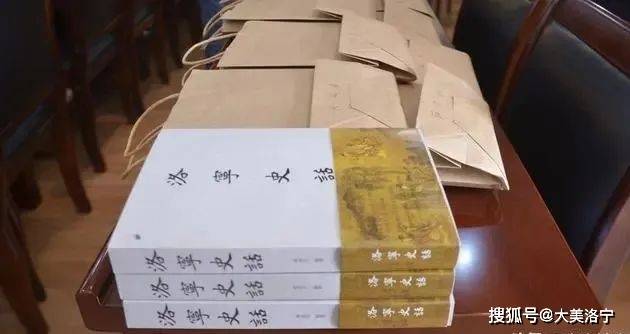
黾池和蠡城
在中国古代史上,“崤函”和“崤渑”经常连在一起。“崤函”指的是崤山和函谷关,“崤渑”指的是崤山和渑池。
渑池,古称“黾池”,它既是个地名,也是个县名。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个渑池县,殊不知这个渑池和古代的黾池并不在一个地方。
古代的黾池究竟在哪里?且看《水经注》所记:
洛水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城西有坞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黾池县治,南对金门坞,水南五里,旧宜阳县治也。
又东北过宜阳县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此自别山,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昔汉光武破赤眉樊崇,积甲仗与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际有池,池水东南流,水侧有一池,世谓之黾池矣。
这两段话充分表明,黾池作为一个地名,最早在今宜阳汉山上,这里过去有个“小熊耳山”,山上有一个水池,池里有一种虫子叫“黾”,故名“黾池”。可黾池作为一个县治最早是在蠡城,其城西有坞水,城池就建在北边约25丈高的山原上,其具体方位是:南对金门坞,在洛河南岸五里,也曾经是旧宜阳县治。
 洛宁县蠡城遗址(坞东村南部)
洛宁县蠡城遗址(坞东村南部)
根据郦道元所标注洛河水自西向东流经的位置,此地应该指的是现在洛宁城西的坞西、坞东之间。它的东南方向正好面对金门川。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时的黾池县绝不在现在的渑池这个地方。
对此,《方舆纪要》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渑池旧理蠡城,今县西有蠡城邑。《水经注》解云,蠡城南对金门坞。属永宁县,以洛水为界。”
那么,蠡城又建于何时?这里又是什么时候做过黾池县治呢?有关史料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继位。同年代汉称帝,国号魏,年号黄初,迁都洛阳。始设五都(洛阳、长安、谯、许昌、邺),开崤道,建蠡城,置黾池,增编制,置屯田都尉。”
由此可见,所谓“设五都,开崤道,建蠡城,置黾池”,这几件事都是曹操的继承人曹丕干的。至于曹操当年路过此地,这里还仅仅是个城池而已。如明人曹学佺的《名胜志》所记:“曹操移县西六十五里之蠡城,贾逵为令时所理也。”这里所说的“县西”指的是位于福昌的宜阳县,从福昌到洛宁坞西一带也就是30公里左右。
另《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载:“逵除黾池令……时县寄治蠡城。”这又说明,在贾逵时期,蠡城已成为黾池县治,而且,贾逵还在这里当过县令。那么,贾逵为何许人也?他是什么时候在这里为“令”呢?
贾逵(180-234),字梁道,河东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人,系三国时魏之名臣,曾辅佐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三代国君。武帝时,曾任渑池令、弘农太守、丞相主簿、谏议大夫等职;文帝时,曾任邺令、魏郡、太守、豫州刺史等职;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也为辅佐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贾逵虽出身于望族门第,然其少孤家贫,缺吃少穿。每到冬天,他穷得连一条裤子都穿不起。据说有一天,他去舅舅柳孚家里住宿,天明后没啥穿就把他舅舅的裤子穿走了,以至在街坊邻居中成为笑谈。然而,贾逵穷而有志,他自幼习武,常以摆兵布阵为游戏,其祖父甚奇异之,曾夸奖他说:“汝大必为将。”并向他口授兵法数万言。
建安九年(204年),贾逵任渑池令(这和曹丕设县相错16年,姑且存疑)。在任职期间,袁绍的外甥、并州(在今山西晋阳、太原一带)刺史高干反叛,驻兵壶关(今山西长治),曹操遣乐进、李典攻壶关而不下。接着,河内张晟、河东卫固、弘农张琰均举兵响应,声势浩大,曹操再派夏侯渊、夏侯尚领兵追剿,叛军与魏军转战于崤黾之间。忽一日,叛军兵临黾池,贾逵立即跑到弘农向张琰求救,当时他不知张琰已反,等他到了弘农才得知实情,想返回又怕张琰抓他,情急之下,就假装跑来和张琰一起共谋反叛,在赢得张琰的信任之后,贾逵以蠡城“城堑不固”为由,要求张琰派兵修缮城池。待张琰派兵来到蠡城以后,贾逵就趁机把他们全部诛杀,并下令筑城据守。不久,张琰败亡,便随高干出逃了。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西征马超至弘农,认为弘农“此西道之要”,遂将贾逵升任弘农太守。他把贾逵召进军帐议事,听了贾逵的建议,曹操很高兴,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的官吏悉如贾逵,吾何忧?”由此可见曹操对贾逵何等器重。果然,曹操在贾逵的辅佐下,于弘农发兵,大败马超于潼关,贾逵也因此被提拔为丞相主簿。
贾逵卒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终年54岁。
也许,在渑池人看来,古黾池和现在的渑池基本是一回事。且看《渑池县志》是怎样说的:渑池之名来源于古水池名,本名黾池,以池内注水生黾(一种水虫)而得名。黾池,上古属豫州,西周时为雒都(今洛阳)边邑,春秋时先属虢、后属郑。战国时韩灭郑,渑池属韩。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秦赵会盟于西河外黾池,今县城西有古秦赵会盟台遗址。
按这种说法,渑池县城应该一直在今渑池县境内。然而,它并未提及县城的治所最早在哪里,只是以此地原有一个“注水生黾”的水池和“秦赵会盟台”为主要依据。
关于秦赵会盟之地,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昭襄王三次发兵攻赵,赵国失利而不屈服。秦为征服赵,又开始政治与外交上的斗争。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人告诉赵惠文王,为使两国和好,双方可在渑池会盟。陪同赵王前往的是赵国上大夫蔺相如。秦王与赵王会饮时,胁迫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入秦史,使赵王感到无比难堪。这时,蔺相如正气凛然地强请秦王击缶,亦令赵国史官记入赵史。秦国官员不服,胁令赵国割十五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迫请秦国割都城咸阳给赵王祝寿。如此针锋相对,舌枪唇剑,直到宴会终了,秦王也未能捞到丝毫便宜,只得与赵王言归于好。为表示偃旗息鼓,停止战争,双方士兵捧土埋藏兵器以示友好,遂成会盟高台。
虽然秦赵会盟是事实,但会盟的地点在哪里,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按常理推断,秦国的国都在陕西咸阳,赵国的国都在河北邯郸,他们会盟的地点应该在从中原到关中的大道旁,同时也应该在两国的交界附近。问题是那时从中原到关中的大道到底在哪里?渑池又在哪里?如果说这条大道在今渑池、新安一线,那么“秦赵会盟台”在今渑池附近也就顺理成章;如果说这条大道在洛河川里,则应该另当别论了。
另据《晋史》记载:“王镇恶进军渑池,遣毛德祖擒秦将尹雅于蠡城。”这是东晋末年的事,由此也能说明,直到东晋时期,渑池和蠡城还是在一起的,不然,王镇恶攻渑池,却让毛德祖跑到洛宁境内的“蠡城”捉拿秦将就没有意义了。
至于渑池县治从什么时候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宋朝的《太平环宇记》中有明确记载,说是从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令移于今县西十三里故沔池县为理。隋大业元年(605年)又移于县东二十五里之新安,十二年(617年)复移理大坞城。唐贞观三年(629年)于大坞城移于今理,立谷州”。可见,现在的渑池在南北朝时称为“沔池”,后来才改成“渑池”,而洛宁境内的黾池也只能改作“南渑池”了。
总之,无论是“黾池”也罢,“蠡城”也罢,“南道”也罢,“北道”也罢,这些都是历史的陈迹,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毕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自古至今数千年来,从洛阳到潼关穿越崤山腹地,绝不是仅有一条通道。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出于不同的需要,人们总会选择一条适合于自己的道路。
最后,再讲一个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洛宁长水乡的孟家峪村。说是在三国时有一个孝子姓孟,名宗,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十分贫寒,母子相依为命。一天,母亲病重,想吃竹笋,但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上哪儿去找竹笋?孟宗无可奈何,就跑到竹林里抱着竹子痛哭起来。他的孝心终于感动了天地,只见四周的冰雪都融化了,草木也返青了,竹园里一下子冒出了一棵竹笋。孟宗喜出望外,连忙把竹笋掰下来拿回家让母亲吃了,没想到他母亲一吃竹笋病也痊愈了。后人曾作诗称赞之:
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
须臾冬笋出,天意招平安。
 孟宗哭竹
孟宗哭竹
关于孟宗所处的年代,现在大部分资料上都说是三国,也有人说是东汉。另据《河南孟氏族谱》记载,河南孟氏十八世孙“孟宗,字恭武,其孙孟吴曾为永宁令,后升为右御史、司空。二十四孝之一,有哭竹生笋之事”。由此可见,此事确实发生在洛宁。只是这里所说既然他孙子任过永宁令,永宁是在隋朝以后大有的县名,从三国到隋朝相隔三百多年,至少传到十世以上。如按此推算,孟宗最早也只能是南北朝时期的人。
(来源:周流宗《洛宁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