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何必曾相逢
——《舞笛拾零三部曲》读后感
张竹伸

我和舞笛老师相知大概也有五六年了,记得我看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有关一个骨笛的考古发现,不知是否和他的笔名有关?我的直觉舞应该是舞阳的舞,笛字应该和这个骨笛的故事有关。后读罢《山吟海叹》中的《初音笛声万古扬》我的感觉不谬——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地就是他的故乡。
他是河南平顶山矿区的知名作家,四十多年的矿工生涯里笔墨耕耘已经非常成熟,颇有成就,一堆的头衔让我仰慕,他文字让我倍感亲切。我虽然出生在武汉,但八个月大就随父母来到北大荒的佳木斯支援边疆,一直生活到现在,对老家对中原文化很向往,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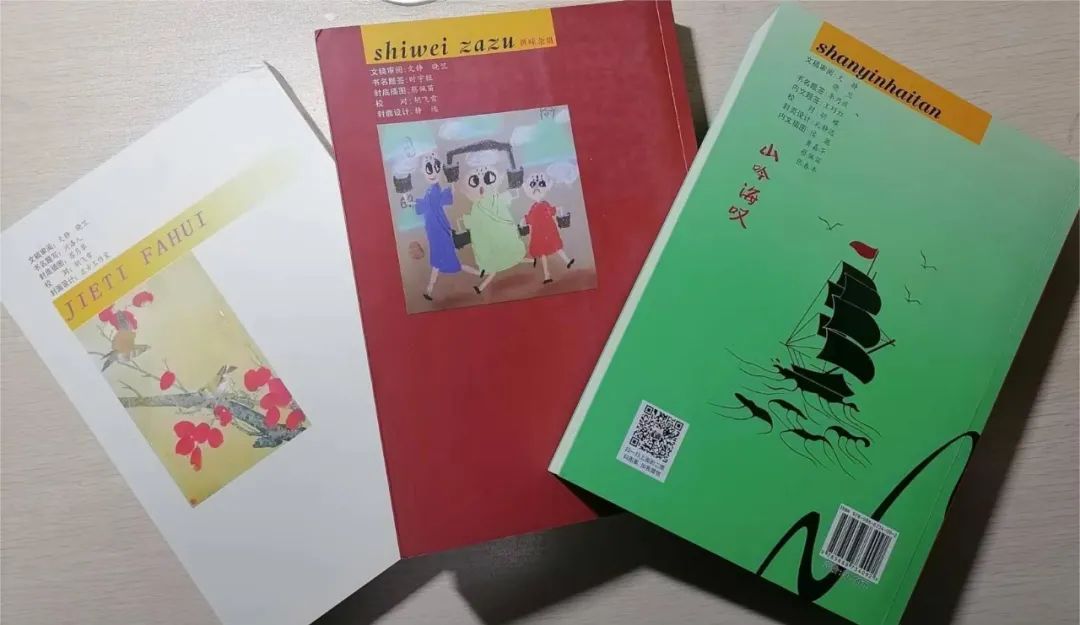
对舞笛老师的文字也特别的关注和亲切,看到妙处情不自禁的留言评论一番,当时并没觉得班门弄斧,只是有点憋不住想说,平时也喜欢留言点评。没想到舞笛老师竟然和我取得了联系,多有交流,几年下来来受益匪浅,这是网络带给我们的缘分。
前几年他的第一本拾零集《借题发挥》成书,就给我寄过来一本,让我爱不释手,因为我也喜欢在别人的文章后面留言借题发挥,只是我写的往往很短,没有老师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去年又寄来两本新作——《世味杂俎》和《山吟海叹》,三部书各有不同的侧重和题材倾向,《借题发挥》侧重对感人作品进行品鉴,这后两本内容则分别侧重于典型人物故事和中华优良历史文化的颂扬,同样让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更喜欢旅游和写游记及拾零感怀。相同的兴趣爱好往往是友谊的基础,哪怕素不相识相隔万里。
人的一生认识的人应该很多,生活的圈子再小也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什么的。但真正能兴趣爱好相同的却不多,知音就更少了,“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就在于可遇不可求这种知音遇到是缘分,遇不到是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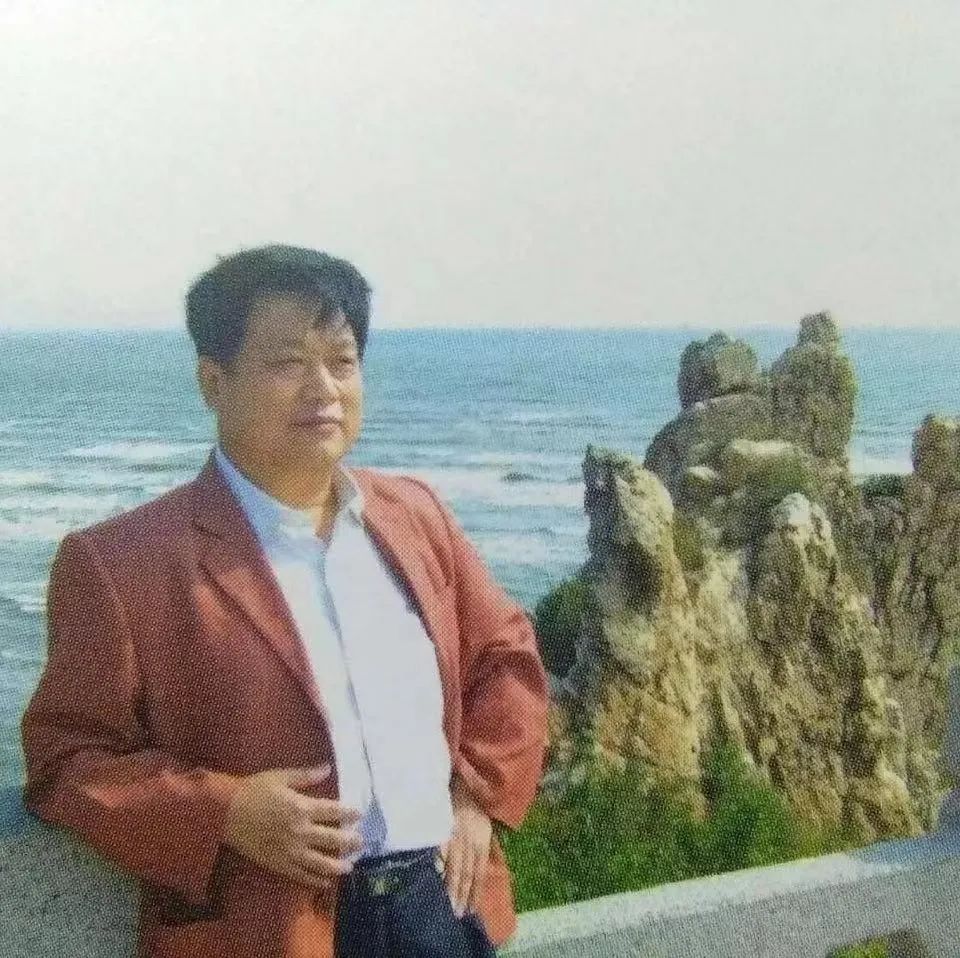
喜欢文字的人往往习惯于在文海中徜徉,欣赏文字也欣赏人,通过文字了解人,了解他的情怀、思想,却未必见过面。我和舞笛老师相识就是始于文字上的偶遇,他是河南平顶山市的知名作家,擅长散文,或者说是杂文。
他的散文有点不同于我们习惯的散文,如杨朔的抒情散文,朱自清、冰心的写景美文,更不同于鲁迅夹枪带棒的针砭时弊的杂文,甚至会把小说写成散文。他的文字有点寓教于乐广征博引的科普类味道,让人读了长知识增见闻,是那种很温情的类型。我是在《星期八散文家园》平台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应该是《生死夫妻生死情》吧,一看就被吸引了,感觉与众不同。后来有读到几篇,字里行间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鲜严谨,有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人物的音容笑貌,还有现代知识的普及穿插,既传授知识又不呆板,教导于无形之中,语言诙谐幽默风趣寓教于乐,让人很容易理解他讲的道理。他的文字精炼、温情、富宇哲理娓娓道来,栩栩如生的历史名人和现代人便活跃在眼前,不管是借题发挥也好,还是人文景观的讲解也好,都生动而又活泼有血有肉,夹诉夹议不似说教更像聊天拉家常。
一个人生而不凡,死而不朽的一定是思想,而思想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思想,人云亦云不是思想。他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是很勤奋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尽量都要到实地考察一番,从资料中挖掘,非常认真,下笔有据,所以有说服力。很多大家熟知的历史故事,人文景观他都能从另一个角度重辟蹊径来解读思考,不落俗套且常有新意。尤其他对名胜古迹并不注重从景物上描绘,而是从文化内涵上挖掘,让千百年的山水园林有了人文的灵魂,有了诗韵名人的滋润,让美丽的景物平添了灵气和仙韵。
舞笛老师虽然还没有显赫的声望,但和我们这些草根文学爱好者比还是成绩斐然,据说他以前出过两部书?经过不懈笔耕,这几年先后又出版了三部书,即“舞笛拾零三部曲”——《借题发挥》《山吟海叹》《世味杂俎》,合起来达百万字之巨,摆在我的床头柜上,时不时看上一两篇。
我也是个喜欢文学的草根作者,文化不高,经历很多,总想把自己经历的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出来,但受条件限制有点难度,但舞笛老师给我做了个榜样,成为我学习的目标。他认真刻苦的治学精神,对读者负责的严谨态度都令人佩服,纵观古今名人大咖都是从草根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凭一首诗,一篇文章而名垂千古的,即使有,我也不相信他一生仅写一篇。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日积月累的积淀,一定有着“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越甚至爆发,不熟悉不喜欢的东西不可能信手拈来就一举成名。
更有些名人在世时不愠不火,不为世人熟知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才熠熠生辉,大浪淘汰地是虚假的灰尘锈迹,或者远离生活的无病呻吟,乃至与老百姓离心离德的东西,淘去的都是糟粕,留下的才是精华。
那些永恒不朽的东西一定是人类的共情,人性的追求,真善美的东西。
我也喜欢旅游,游山玩水,仿古探幽,在山水园林中陶冶情操,在名胜古迹的人文典故中与古人先贤们对视神思。再美的风景没有人的欣赏,没有文化的加持就是荒山野岭,有了人的参与,有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才能被赋予灵魂,有诗词文章的点缀升华才叫名胜古迹,这里的名和迹都是人的名或者人的事迹和足迹。例如他的《山吟海叹》里的《武汉三吟》《感悟泰山文化》《古都开封三叹》《南国红豆》《永不消逝的钟声》等篇章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山水文化升华。舞笛老师在挖掘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结合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赋予了景观背后历史文化的厚重,传承及升华。
长江上的黄鹤楼如果没有千年的诗文、传说、故事、名人的荟萃,只怕很难在十多次的毁灭中屡毁屡建,越建越壮丽。运河枫桥头的寒山寺若是没有晚唐落魄才子张继的那首传世名诗《枫桥夜泊》的灵魂附加,恐怕亦如其它众寺般湮灭与历史尘埃不知所终了。可恰恰因为这首小诗,才使得那清越凄切的钟声才穿越千年时空而没有消逝。世人皆知的杭州西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人物传说,诗词典故,名人轶事就是一个大水泡子,这样的水泡子到处都有,也有风景不错的地方,可除了养鱼又有什么用呢?可舞笛却能从清冽的碧波中提纯出诗词和作者伟大的思想与人格魅力,而令人对这方大水塘愈加敬畏。
上个月刚刚从大庆回来,大庆号称千湖之城,大水泡子芦苇荡随处可见,夏天应该好看,冬天总感觉荒凉。
我两次去江南,去西湖游览,山水依旧,认知却是叠加的,我喜欢跟在导游后面听讲解、听故事、看实景,把故事里的“人”和现场的“物”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生动的人文景观,哪怕是神话故事,在现场的感觉和书里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很有代入感,很多画面在心里鲜活起来。比如我在飞来峰一边走一边听导游讲济公的故事,仿佛济公就在身边嬉笑怒骂,时隐时现。
我喜欢古诗词,更佩服舞笛老师文章里介绍的诗词名家,读诗、学诗、写诗,学习他们的情怀,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名人轶事分外令我心动,包括他们的命运多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包括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还有“位卑未敢忘忧国”壮志未酬身先老,空叹报国无处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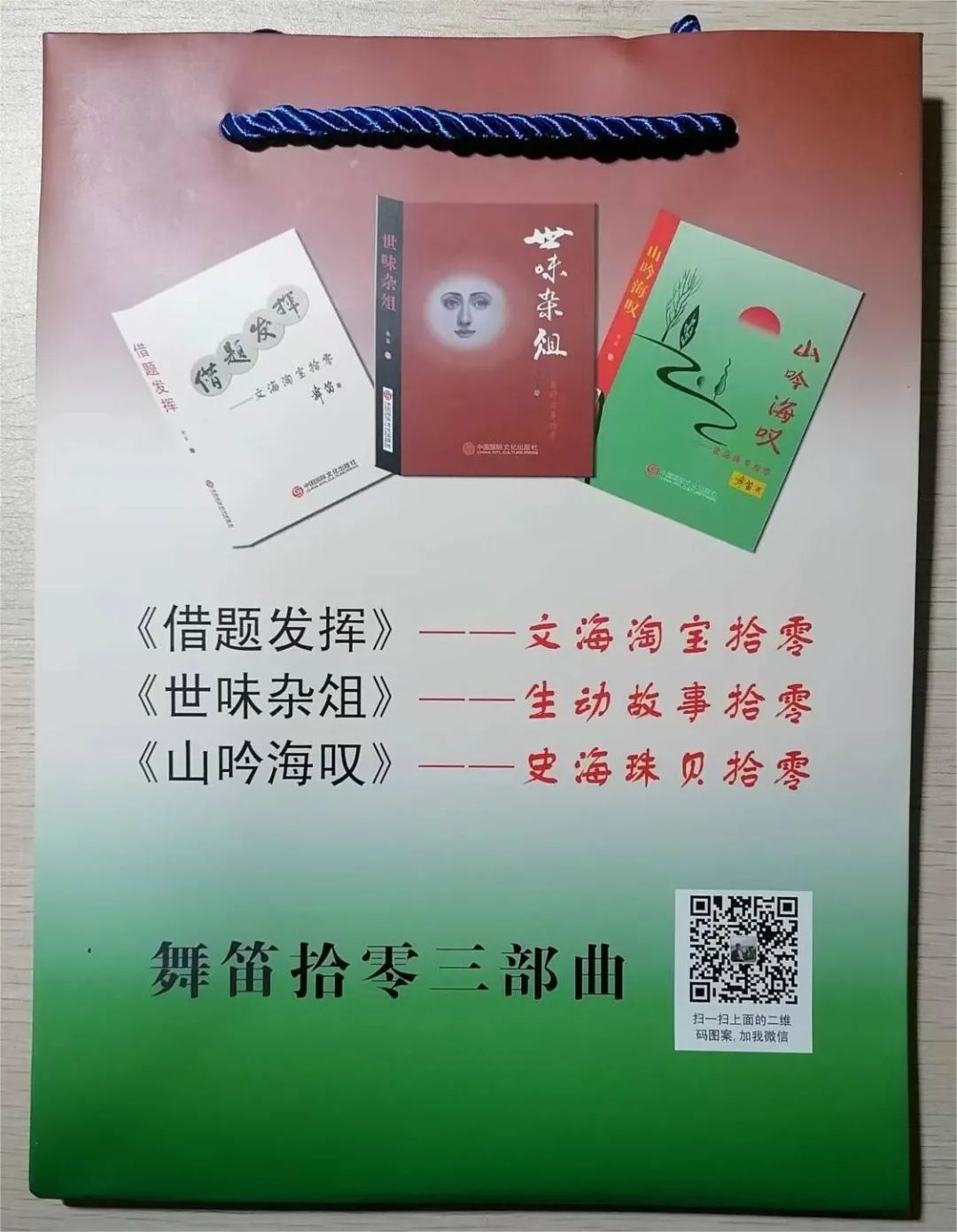
还有岳飞的忠心耿耿,战功赫赫却冤死风波亭的悲壮,虽死犹荣,忠魂不灭,《满江红》读了一遍又一遍,仍然心潮澎湃。李清照、柳永、唐婉、朱淑真等婉约派词人的悲惨遭遇更让人心疼和惋惜,正是这些不幸的人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中靠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创造了文学的奇迹,将诗词耸入一个又一个高峰。试想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或许不能取得那么伟大的成就,正所谓苦难成就诗人也成就了文学。
如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诗仙词圣,伟大的诗人若不经历那么多坎坷,不定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总觉得荣华富贵金钱权力都是过眼云烟,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永恒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什么精神和思想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具体地说只有文化才最有历史价值。据说舞笛先生始终把政治家富兰克林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如果你不想一死就被忘记,要么写点值得读的东西,要么做点值得写的事情。”他在挖掘古人做的那些“值得写的事情”的同时,也在坚持书写“值得读的文章”。人类文明不断在进步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还在闪闪发光,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东西就是文明,文化和精神,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人类也就消失了。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生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创造和深化、传承文化!
喜欢文字的人一般都是多愁善感的,古代的文人如此,现代的也差不多,连我这个苦力文学爱好者也有点悲秋忧月,忧天惜人了,常为一篇文字,一个故事感动的一塌糊涂,不能自持,都说一字之师,舞笛老师的这三本书够我消化余生了。

来源:星期八文化沙龙



【作者简介】张竹伸,男,笔名:草茂竹伸,原名:张族琛。湖北武汉生人,现住佳木斯。黑龙江省佳木斯作家协会会员。90年代开始在厂报《电机报》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多发在《佳木斯日报》《三江晚报》以及《佳木斯作家》《星期八散文天地》公众号平台。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