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吟海叹》诗酬和
——读舞笛《山吟海叹》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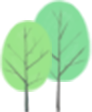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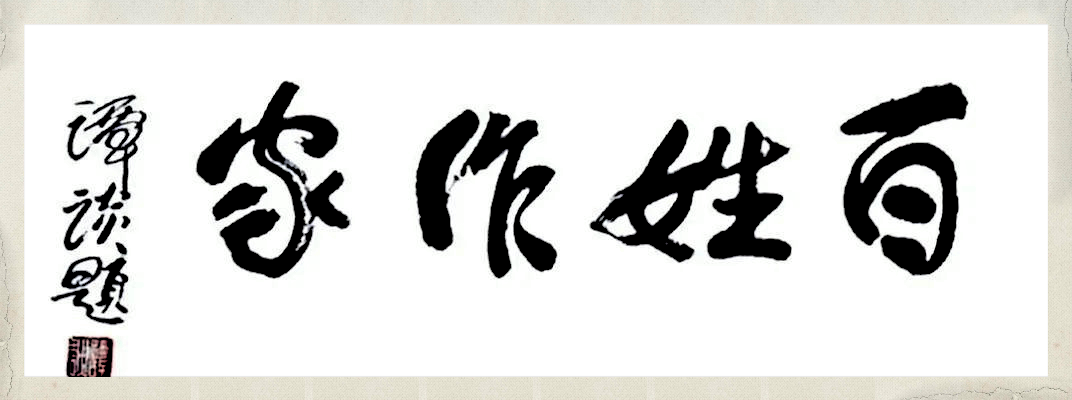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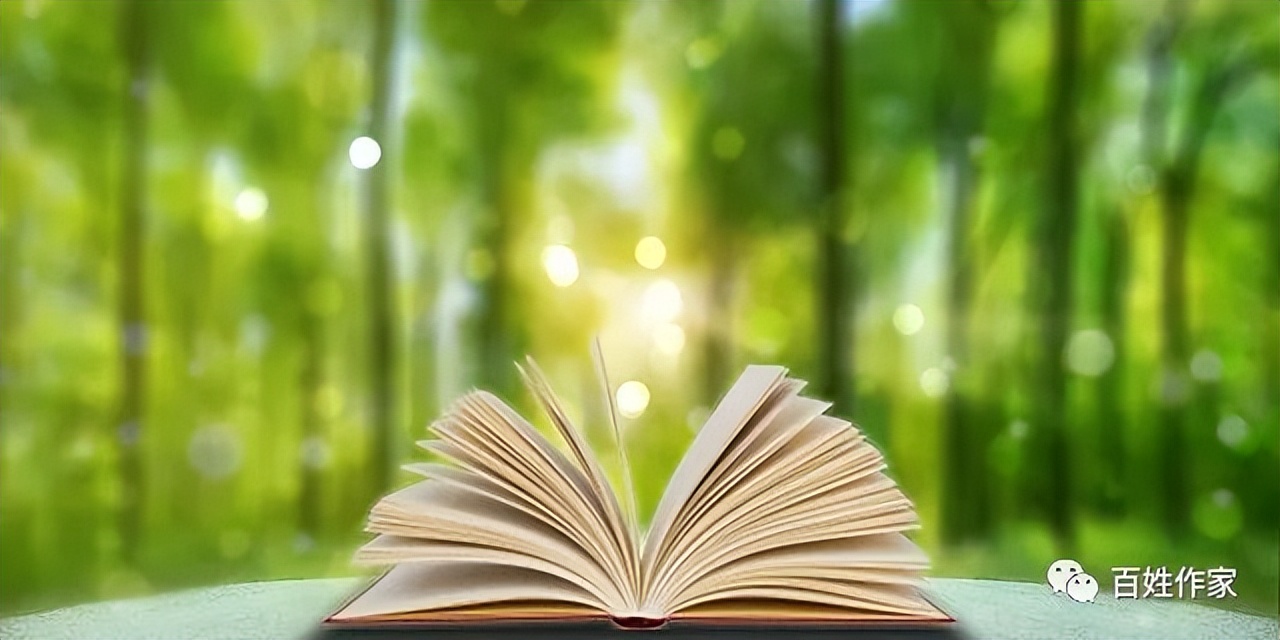
《山吟海叹》诗酬和
——读舞笛《山吟海叹》随感
文/全兴
欲说还休的2022年不堪回首,即便如此,蓦然回首之时,那灯火阑珊处,同样有若许让你怦然心动的瞬间难以忘怀,无论是喜还是悲。
新冠防疫封控静默管理时期,一次次的核酸检测,让你不厌其烦,却又无奈且无语;一层层的加码严控,让你寸步难行还得感恩戴德,那时候,安抚你“未阳”之心的灵丹,就是静下心来读书。
“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在2022年即将同我们挥手告别时,新冠疫情防范竟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在一片片“欣欣向阳”的惊恐万状中,无论是在“林阴”小道穿行,还是冲出“阳关”皆故人,抚平你心头创伤的妙药,还是静下心来读书最有效。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是年8月,我告别职场,退出江湖——“隐退江湖归深山,只为余生得安宁。”诀别日复一日的签到打卡,大同小异的复制粘贴,言不由衷的慷慨陈词,装腔作势的正襟危坐,弱不禁风的义正辞严,没完没了连篇套话,劳心费神的会检考评,此起彼伏的投票点赞,得意忘形的觥筹交错,阿谀谄媚下的阳奉阴违,扯淡专业里的专业扯淡,卸下苦我久矣的虚伪面具,放飞禁锢已久的疲劳身心,在找寻那个曾经丢失的率性真我时,倏然间却有一种释然后的茫然。
是年8月26日,舞笛有约,我们在久久封控间歇的忐忑中再会,在酣饮中畅聊,在开怀中抒情,临别时《舞笛拾零三部曲》成了那次约会的至诚信物,这份2022年最珍贵的礼物,是我那时的雨中伞,彼刻的雪中炭。
概因年少时物质精神的双重匮乏,对书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至今,对好书特别是新书更是珍爱有加,包括《山吟海叹》在内的这三部曲也不例外。有朋友曾这样说:如今接受作者赠书也不算少见,但作为草根作家的舞笛先生的著作这么有见地有深度的作品却不多见,这话我也认同,因为在我通读之后也是这么一种感受——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认识更是不从众流俗,其语言其思想甚是深刻。在此,我最想和文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您真的认为舞笛的作品没什么了不起的话,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您没读到底,但凡通读者,定然会频频点头,暗暗称赞。深刻的的道理只有细心领会,才能受教。
三个月的魔鬼式的三维软件学习,是我“欲扬先抑”暂时珍藏而没打开的一个美丽堂皇借口,10月开始阅读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我后来拜读舞笛《山吟海叹》的热身。
在2022的阴阳焦虑中,我与舞笛先生的每一次畅聊中,都离不开疫情下文学的表达,其中有“山吟”也有“海叹”。
是年12月28日,我郑重其事地打开了期待已久的《舞笛拾零三部曲》中的《山吟海叹》。页页散发出的别样墨香和字里行间沁人心脾的书香,令我神清气爽。跨年度8天的披阅,置身世外,和山峦同吟,与河海共叹,正是在这一吟一叹中,才真正领略到了舞笛先生的生花妙笔。当合上读完35万字后的第394页,掩卷长思,醉享西湖的诗韵之美,静听骨笛的天籁之音,陶醉古往今来的感慨杂言,以史诗为主线串成的一颗颗珠贝,无不充满着诗意,长思之余,我也不揣狗尾续貂,借题发挥一番,以《<山吟海叹>诗酬和》入题聊表感怀。
洋洋洒洒的《山吟海叹》,开篇便是惊艳的《千年诗光照西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之柔美与东海之浩瀚,钱塘江潮之壮观,相映成趣,动静相应,天地相合,古今集成,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胜境,《千年诗光照西湖》我未至神已往。众人游览西湖,大多饱的是眼福,那是视角美带给的享受,而舞笛则不仅饱了眼福,还醉了心灵——他读透了碧波荡漾下的一湖诗词,那是他最大的收获,同时也把这丰盈的收获带给了我们一同分享。
舞笛的笔下,十二位大诗人,从唐代到晚清,一个接一个地姗姗而来,皆在用烁目之诗光词韵铺满西子湖,正如十二个月连成一个年那样,使诗意的西子湖,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叫你“能不忆江南”的春之西子湖;有“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之西子湖;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怎一个愁字了得”的秋之西子湖;还有“耐得寒霜是此枝”的冬之西子湖,谁能不说“中”!
四季的诗意西子湖,白堤和苏堤是诗人吟叹后的疏浚实干,是林升和李清照的深情呼唤,是放翁和岳飞的慨然悲叹,更是龚自珍和秋瑾的愤怒呐喊。
诗光使西子湖“淡妆浓抺总相宜”,诗意的西湖,别样的西湖,“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飞把自己的忠魂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还有他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使西湖更加厚重而悲壮,柔美中多了几分刚烈;“只留清白在人间”,“生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无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忠贞无二的万世楷模于谦,西湖是他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的坐标,他的忠贞,不仅挽救了大明,更把自己的清白和忠烈气节留在了人间。他的风骨不仅在诗里,也在史里,更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间。
十二位诗人的西湖不是西湖的全部,十二位吟咏西湖的诗也不是他们诗的全部,但诗人用诗光描绘的诗意西湖,让人流连忘返,光照千秋。
舞笛笔下的诗光,既有如日之灼灼的烈光,也有如明月之皎洁的皓光,李清照、朱淑真两位女诗人与西湖的相会,使诗光更加绚烂。如果少了这两位诗人的咏叹,西湖的美就会少却几许神韵。舞笛先生的精心,特别是提供了散落于史海中朱淑真的诗词,可见其对西湖的情怀,对女诗人的尊崇,使西湖凭增了几分阴柔和凄丽,也填补了不少读者领悟古诗的以份空白,可谓是匠心独运。
跳出西湖看西湖,舞笛这篇《千秋诗光照西湖》,在诗词的平仄里,无不充满诗人家国情怀,在诗光的虹华中,无不流露着舞笛先生怀古喻今的别样情愫。西湖是个舞美的平台,一个又一个诗人闪亮登场,有诗光照耀,有舞笛编排,读者享受的是无比丰富的文学与精神之盛宴。
品享了《千秋诗光照西湖》唱和,再听一曲贾湖骨笛奏响的天籁之音。
在中原,在河南,在舞阳,有舞笛的乡愁,更有中华儿女的古音。9000多年来,初音笛声悠悠万古飞扬,正如他在引言中写道:“自此,我们找到了华夏的初音,智慧的火花,人类的童年!”
这一篇,生于斯长于斯的舞笛先生,是描写骨笛的再合适不过的不二人选。
他还曾向我讲述自己舞笛笔名的来历,从武狄到舞笛,决不仅仅是网名的变换,更是他文学创新探索触角的扩展。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远方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随着曼妙的歌声,舞笛先生把我们带到了史前的泥河洼,他依照曼妙想象,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仙鹤在泥河洼凤凰般轻飞漫舞的唯美画面,以及远古笛音里飘荡的悠悠乡愁。
我常想,如果谪仙李白再世,饮着贾湖酒,听着骨笛音,品着舞笛文,吟一遍《静夜思》也会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绝对是诗兴大发,再创佳作。诗仙辞别时,也会感慨:泥河洼水深千尺,不及舞笛送我情。
也许,这样的天籁之音,有了诗词的应和,才更精妙绝伦,也许这样的千古初音,没有诗文,会更质朴自然。然而,有了这样大音作背景,山吟海叹诗词酬和才更动听。
中华文明从9800年前的舞阳骨笛奏响初音出发,步履蹒跚,在6500年前伏羲带领我们见到了文明的晨曦,再至5000年前的炎黄打造了我们文明的雏形,3000年前,禹和启开辟了我们的文明的新征程,商代的甲骨文为我们的文明作了标记,在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841年,我们的文明才有了准确的纪年坐标。
文字的演化,文化的演变,文明的演进,离不开中原这片厚土的滋养,舞笛先生在《中原走笔都说中》《函谷紫气万古魂》和《神奇的犹龙遗迹》《舞阳侯樊哙筑城记》《伏牛山头望银河》《“关林”琐话》《古都开封三叹》《走近那远古代的华夏始祖》诸文中,都对中原的人文地理、传说奇闻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虽然没有象《千秋诗光照西湖》那样,以西湖为平台,以诗为引线进行大开大合的抒情感怀,但中原大地的文化厚土滋养出来的文明中,何尝不是用无数先人们写就的史诗,在一篇篇用包含着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串成的中原珍贝何尝不是无韵之诗史,在字里行间引用的诗句、楹联,为描绘中原文化起到了画龙点晴的作用,在生动有趣之余,读起来耐人寻味。不在诗多,而在诗精,更在恰到好处的妙用。
舞笛的走笔,从中原出发,向西在《洪洞大槐树》的繁枝茂叶中寻找生命演绎的文化符号,又一次地把大槐树与中原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血泪的牵连,在舞笛的笔下,这种血泪谱写的文化音符,都被挖掘出来,让读者思考我们民族的苦难结果,还原一种凄惨的灾难场景。古老的中原在一次次的战乱后的迁徙中又一次涅槃重生,何其有幸,在那群队伍中有定居舞阳贾湖泥河洼的舞笛先生的祖先,也有在南阳落户的我的祖上,我每一次从南阳石桥镇老街走过时,那棵垂而不朽的老槐树不仅仅是我的乡愁,也承载着从洪洞大槐树到南阳大槐树的迁徙血泪史。
唯一不同的是,舞笛先生有骨笛初音引以为豪,我则是在白河畔洗耳恭听。
随着舞笛的足迹和笔锋,他把我们带到西北的天山之上。一篇《天山之上思英雄》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国难当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晚清,这两位民族英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确保边疆安全方面,居功至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舞笛以独特的视角,别样的笔法对这两位彪炳青史的伟大英雄及其无量功绩进行了阐述,值得点赞。
我也曾踏着舞笛先生的足迹,于2016年在参加同学聚会时,提前一天到福州,并循声三坊七巷参观,还专门到林则徐纪念馆和林则徐出生地观瞻凭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亲眼目睹一下那两首颔联诗句,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英雄真迹。
后来又一位民族英雄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令人动容,让人泪目。还有后来的千万湘女上天山的感人一幕,我在网上看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援建的《献给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奋斗终身的湘女们》的纪念碑时,忍不住留下了热泪。谁说女子不如男,她们何尝不是左宗棠精神的传承人?
天山不仅有湖湘儿女,中原儿女也没有缺席,舞笛先生的家人,我的亲人们也有在新疆安家定居,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边疆,他们何尝不是天山之上英雄的追随者?十五的月亮照在中原也照在天山,中州的儿女生长于黄淮也奉献于边关,先辈们用铁血收复的国土还需全民族来共同守护,在这方面,中华儿女没有辜负先烈的期望。
读了这篇文章,我才深深地感觉到他在文章中的一段关于“护照”说辞这个小插曲的深刻意义。
这又让我想起了近几年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一个志愿军老兵去韩国旅游,在拿护照时动作慢了点,韩国女海关员便没好气的说:难道你以前没来过首尔?老兵答:来过一次。女海关员说:那为什么不提前把护照拿出来?老兵:我上次来没人检查我的护照。女海关员:不可能!外国人来韩都要检查护照!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老兵答:1951年元月份,当时开坦克来的,没有一个韩国人查我的护照!
没有先辈先烈们的赴汤蹈火,哪有今天的中华振翅高飞?
“市井有谁知国土?”读完这篇《天山之上思英雄》后,放目时下我们的国泰民安,才可以告慰先烈。
“山吟”的不仅仅是天山,还有《感悟泰山文化》,还有《避暑山庄山外山》,舞笛先生为我们呈上的不仅仅是“一览众山小”的人文泰山,还有那风月无边、泰山石敢当等动人故事。其中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历代皇帝的封禅,五岳独尊,还有泰山挑夫精神、杜甫的诗和平民将军诗人冯玉祥的平民情怀。
知识性,已成之为舞笛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
在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里,舞笛笔下的山外山的确更吸引人,但更吸引我的是,他文中引用康熙的那首诗:“纵目湖山干转留,白云枕间报深秋。晚上自有初佳处,未若此峰景最幽”。相比于我一首也记不全的拥有“万岁万首诗皇帝”的其孙子乾隆帝,他爷爷的这首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历史上,父子皇帝一串串,父皇子帝兼诗人也不鲜见,爷皇孙帝虽屈指可数但也能找得出几对,可爷诗人孙诗人实在凤毛麟角,唯一遗憾的是这对爷孙诗人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所谓的“康乾盛世”,而空乏经典诗篇。
刘禹锡诗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果不其然,所谓的真龙天子,想让山出名,与诸仙相比,还是差点道行。
相比舞笛文中的山外山及诗外诗,沉思后我更感慨那场外场——在“木兰围场”这个皇家禁地狩猎场附近,震憾世界的塞罕坝林海里的机械林场,想必字里行间也有林海之叹吧。
林海风声与骨笛初音之异曲同工之妙,虽没有诗,却处处有诗意。
山吟之余,海叹有加,舞笛的思索不仅仅是林海,还有他的“思海”。从华东上海的《沪路溯源,》到苏州寒山寺《永不消失的钟声》、镇江的《红豆南国》,到西南的《峨眉山猴王让道委座谜解》《“古典处女”的神秘面纱被意外抖开》《云散我未散 日灭我不灭》《东巴文化印象》,再到《寻梦客家人》,还有华中的《武汉三吟》,不仅如此,舞笛在山吟海叹之余,不时地给读者来个小插曲,《可悲可叹的中国古代捐官制度》《古代官服话外音》,还有充满激情和梦想交织的《绿茵场狂想曲》,当然《妙趣无穷的回文诗》更是余味无穷。
限于篇幅,不便一一展开。这本书的序言《处处留心有文章》和校稿感言《见识情怀知风趣 尽在山程水驿中》以及作者后记《视通万里觅洞天 思接千载会先贤》,篇篇文采飞扬,如行云流水,字字珠玑,扣人心弦,令读者赏心悦目,欲罢不能。
这部《山吟海叹》囊括六七十余篇章,计400多页35万字,是一部充盈着诗意的文化随笔性散文集,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共有近两百首词章诗句被引用,从而令作品优美而雅致,使文意更加凝练且且富于哲思。
这正是我用《<山吟海叹>诗酬和》作文章标题的缘由。
诗歌和散文,是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最早形成的两种文体,至今仍在为文学的繁荣而与时俱进,为弘扬华夏文化和丰富文明内容默默奉献着。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九元书》中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舞笛先生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写就的这部《山吟海叹》皆系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且篇篇都是精心打磨而成,无一不凝聚着舞笛先生的思维结晶。让我惊讶的是《峨眉猴王让道委座谜解》《武汉三吟》《避暑山庄山外山》等篇章都是经过30多年的打磨,可谓是细工出细活,精工出精品。
诗是凝练有韵的散文,散文是无韵放飞的诗。两者都是形散而神不散。给人以美的享受,心的愉悦。
泱泱中华,诗海茫茫,千年不衰。如水源远而流长,经久而不息;如酒时长而醇香,历久而弥新。诗者,写景状物抒情也;诗者,寄思扬意言志也。
我曾经写过一篇《诗说》,谈及自己关于诗的观点:诗之美在格;诗之美在韵;诗之情在真;诗之意在切;诗之魅在比;诗之魅在变;诗之意在境;诗之新在炼;诗之新在破。诗之魂在人;诗之魂在心。
一部书中竟有近两百首诗句布洒其中,为文采增辉,为吟叹生韵。舞笛先生曾自嘲“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虽然不工于诗词,但他在行文中对诗词挥洒自如的引用,于不自觉间令作品生出了润心的灵性,强化了散文的灵魂,闪射出夺目的光芒!而且亦由此形成了他的一种创作风格。
我最早读过舞笛先生的《人在旅途》一书,十八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六年前,我又拜读了他的《借题发挥》,这些年,特别是疫情防控这三年,在舞笛先生的诱导下,我在步入创作的道路上,从写诗填词转到写散文,学写小说,何尝不是“借题发挥”?
这本《山吟海叹》,是我2022年最后打开的一本书,也是我2023年率先读完的第一本书。《<山吟海叹>诗酬和》是我今年写的头一篇文章,饱含着对舞笛先生的多年厚爱的一种敬意和致谢之情。
舞笛先生经常和我讲:人这一辈子,要想活得有声有色,要么做点值得写的事情,要么写值得读的文章。
真的为舞笛先生的执着勤奋点赞。岁月向前,山吟海叹撩起绵绵的乡愁和缕缕的思绪,让人回首,听一听万古悠扬的骨笛初音,读一读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岂不快哉!
这部《山吟海叹》何尝不是《武汉三吟》中的古琴台?舞笛先生何尝不是正在抚琴的俞伯牙?我甘当一个打柴的樵夫,愿作舞笛先生的知音,让这一篇篇佳作如高山流水般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和精神家园。
今将白居易的《一七令·诗》和我填的一首《一七令·诗》一并列后,借以酬和舞笛先生的《山吟海叹》——
《一七令·诗》白居易
诗。
绮美,瑰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世间惟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一七令·诗》全兴
诗。
韵美,思飞。
书爱恨,写欢悲。
今古中外,聚合散离。
上星云日月,下故事传奇。
无论律诗绝句,小令长调歌词。
千年吟诵无穷已,最是骚人爱倾依。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作者简介

全兴,本名付春兴,汉族,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工程硕士,从事煤炭企业培训工作20年,有20多篇论文在各级杂志上发表,参与《安全知识百问》一书的编写工作,荣获市级优秀老师,省煤炭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省科技创新先进个人、市青年科技专家等称号。多家网络平台签约作家。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