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路灯》
第三章 蹉跎年华(四)

乃文拿着14元钱往桌上一放,素织问:“这啥钱?咋恁多?”
他说:“玲妹寄的10元,我的助学金1.5元,加上四个周日的推水车钱。”
大姐拿出1元塞给他:“你做个零花钱。就这样,我都感到轻松多了。”
是啊,玲妹这一去,不仅减少一人吃饭,反而还能寄回10元补贴,她肩上的担子当然轻多了。
乃文说:“天无绝人之路,当前的困难一定会很快过去的。”
素织不知想起了什么,说:“可玲一个十几岁的娃子,在黄河边风吹日晒雨淋的,每月10块钱不知咋讨的?这个死王方,把这一摊子撂下,也不管一家老小死活,几个月了连个信都没有。”
他说:“方兄也是不得已,他回去吃住无着,连个信都没写,困难可想而知。"
正说着,王方扛着一袋粮食推门进来了。乃文赶忙去接:“这啥?”
王方:“回来的时候你大哥给磨的玉米面。”
他把面袋接住放下:“借的地还种着吧?”
王方:“队里收回了,上边说'三自一包’,是搞资本主义。你大哥说,要不是借地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乃文脑海里立刻闪出全村浮肿,户绝队灭,借地度荒的一幕……
有一年上边让借地,一口人可借一亩,乃文家借了七亩地,包括三个五保户的三亩,共十亩。他和大哥把小屋快倒的后山墙换了换,把那壮土揽在了玉米上。秋后玉米丰收了,棒槌大的玉米穗堆了一院,从此解决了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也还清了借张元周同学的粮食。
他对大兄的话深有感触,说:“要不是借地,我也上不了大学。”
素织说:“你回去几个月了,安顿好没有,连个信都没有?前天杨娥还问呢,说现正在甄别下放人员、落实有关政策呢。”
王方说:“老家王协没任啥儿,几间房子让兴方失火烧了。我一直住在城里杰三弟家。一天,见了公老么社长,他问我,我向他说明了情况。
他说:“人家想出去还出不去,你咋出去又回来了?你回来,素织和孩子们呢?”
我说:“他们还在西安,不愿回来。”
公老么:“回去、回去,赶快回去!”
我说:“我的户口、粮食关系都转回来了。”
公老么:“叫陈秘书给签个字,拒收,给退回去!”
就这样,队里、公社都不接收,我就回来了。"
素织问:“户粮关系呢?”
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个信封给她,她抽出来看看:“我看杨娥下班了没有。”说着起身出去了。
这是个星期天,乃文正在洇砖往工地送。宝宝跑来说:“小舅,二舅来了,我妈叫你回去。”
晚上他到大姐家问:“二哥呢?”
大姐说:“跟你方哥到菜市场买菜去了。”
每天夜里,外边收市时,不少上年纪的人,都涌到菜市场去买菜农卖剩的菜,一毛钱一堆。一会儿,他俩各拘一大拘烂青菜,气喘吁吁的回来了。
乃文问二兄:“你在单位来,还是在家来?”
通五说:“搞'四清’回来,机关都在大鸣大放,我就请假回家住了几天,顺便来看看你们。”
乃文说:“学校前段很乱,不少学生乱批斗院领导、教授和老师,后来市里派来工作组,才把这股风压了下去。可是没过几天,中央发了个'五·一六’通知,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现正在批工作组呢。批斗、戴高帽、游街可厉害了。”

大姐说:“文弟当个班长,说他是保皇派,经常陪着牛鬼蛇神一块游街。”
通五问:“咋能让你游街?”
乃文说:“工作组进驻时,班里成立'筹委会’,领导让我当主任。班里侯一哲、胡廷机等人不愿意,叫选举产生。我提出辞职不干,学校不愿意,最后一投票,选的还是我。现在说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说我是'保皇派’。我知道过去康、梁六君子是保皇派,他们是保光绪皇帝,我保谁啦?真不明白。可是他们硬叫检讨,还老是说不老实,态度不端正,不让过关。不让过不过,无非是陪领导、教授们站站台,游游街,不准参加他们的破'四革命行动。”
王方:“小小娃家,啥保皇派?人家说我们是运动治国,你看这几年消停过没有?这次不知道又生的什么幺蛾子。”
通五说:“一九五七年,我在郑州上学,高音喇叭里天天吆喝帮助党整风,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谓的'四大’,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可是,后来反右派时,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凡是提意见者统统打成右派分子,送劳改农场改造,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那里,别人咋闹腾咱管不着,你可千万别跟着瞎闹腾。现在斗领导、破'四旧’,的那么多历史文物、玉宝、寺庙都毁掉,将来整这些人时,不知给他们编排啥罪名呢?”
乃文说:“现在学校也停课了,对我们这些'保皇”派’也不管了,我们成了自由分子,别人叫逍遥派。”
大姐说:“你记住,你是上学了,不管别人咋闹,你别忘了学习。”
通五说:“逍遥派好,咱可千万别往这是非窝里卷。
乃文说:“明天我领你到各院校看看吧,可热闹了,比春节、十五都热闹。”通五说:“我想去农场看看玲妹。”
大姐说:“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去农场时叫文弟陪着你,别摸不着路。明天你兄弟俩,她又转向王方,“你去天喜、赖毛家借两辆自行车,让他俩骑着看去。
这几天,他们弟兄俩骑着自行车,游走在大街小巷的游行人群中,看到一拨拨的学生在西安碑林进出,把碑林砸得残碣、断碑,狼藉不堪,面目全非。大专院校的学生,押着戴高帽、打着花脸、剃着阴阳头、衣服褴褛、须发冗长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高呼着口号在游行。
他们在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纺织学院的学生组织宣传组要了大量传单。他们来到冶金学院时,见有学生发“海报”,说第二天上午十点,要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刘澜涛等西北局和陕西省“走资派”十万人的群众大会。
乃文说:“这些高级干部平时难得一见,明天看看去。”

第二天上午,他俩来到体育场。硕大的西安市体育场人头攒动,几乎无立足之地。十点整,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了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中老年人,被一群臂戴红袖章、手持红缨枪、身着绿军装的青年人押着开进会场,低头弯腰站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一个接着一个口冒白沫、声嘶力竭的发言人,在控诉这些人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下午两点了,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汗流浃背。台上一位低头弯腰,胸挂牌子的老年人摇摇晃晃,若不是身后架着的人的支撑,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另一个花白须发、身体微胖的人,身子一软,出溜在台上。一个红卫兵过来,抓住他的衣领:“刘澜涛,你平时的威风都哪儿去了?现在装死狗不是!”
说着打了一耳光。刘扭头低声说了句什么,这个红卫兵说:“同意你的请求。”
他又对别人说:“让他们跪下!”
台上扑扑嗵嗵跪了一大片……
通五说:“这比土改斗地主、恶霸还厉害!不看了,太残忍。我想明天去农场看看玲妹。”
乃文说:“明天我陪你去,她在农场看总机,挺好的。"
他们回来一进门,大姐递过来份电报:“单位叫你赶快回去参加文化革命运动!”
乃文说:“去看看玲妹再走不迟,不在乎这两天。”
通五:“连回家带来这里半月多了,也该回去了。这里有你们,玲那里挺好,我也放心了。”
王方:“明天下午有趟东去的火车,我提前去买张票。”
乃文说:“现在坐车不要钱,明天我去送二哥。”
第二天,大姐借了五毛钱,买了两根油条,一把韭菜,上午包了碗饺子。一家都不吃,二兄也不吃。
大姐说:“你下午要坐车,车上不知有饭没有?我们在家啥时不能吃?你吃吧!”
吃罢饭,他俩到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连门都关不上。乃文扛着二兄的腰,把他推到了车门口,把俩包袱传单递给他。乃文到火车站口买了三毛钱的(口袋里就这三毛钱)花红果,返回身递给二兄。
后来见面,通五说:“多亏那两包传单和那点花红果。我把两包传单放在车厢的接头处,一边一包,我就坐在边上。一路十八、九个小时,连个小手都没解,全凭花红果止渴解饿。下车时,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
乃文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那年方兄回来,一时没活干,一分钱收入没有,一家人整天在死亡线上争扎。你回去给大姐兑的20元,可解决了大问题。
未完待续......
关注洛宁城事
阅读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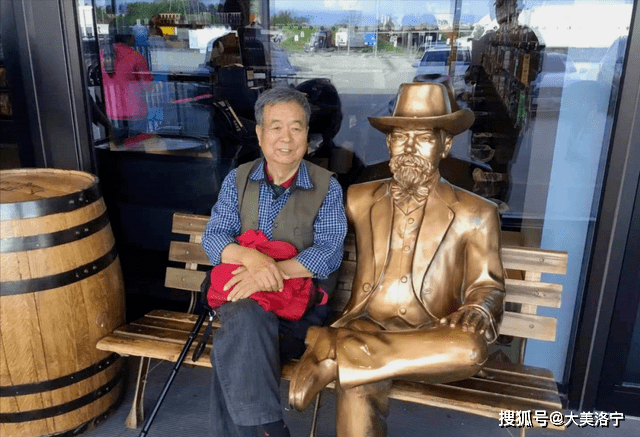
作者简介:卫冠武,男,汉族,1943年元月生,东关村八组人,家住担水堂后祖师阁前。1969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任工程公司副经理,副处职务。后调入总公司劳资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十多年,高级工程师。2003年在劳资处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