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中的安坡
一、安坡村的自然状况,及土地分布
我的故乡安坡,隶属于河南省洛阳市。是洛宁县涧口乡(过去叫人民公社简称公社)下辖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庄。之所以说其小,是因为人口少,占地面积小,相对可用资源就少。别说洛宁县地图了,就是打开我们涧口乡地图,你也很难找到它。别看它小,但在我眼中那却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不光是因为风景秀美,更重要的是,那还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今生今世,永生难忘。
安坡整体趋势,西高东低,面南背北,南陡峭,北平坦。南面与山隔村相望,西面顺山脉绵延而下形成了一道土岭,黄土搅料姜,自上而下有两片洋槐树坡。北面紧靠黄土塬,有良田千亩,故我村的大部分耕地都在塬上。从远处看,安坡村就像是有人特意安放的一把太师椅,当然这个角度只有在南面北望的时候才能发现,从其它三面,很难发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小村落,与世隔绝,就像陶渊元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那宽大的椅背,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即便是冬天最凛冽的西北风,到这儿都得拐个弯,所以冬天不觉得特别冷。
站在村中南望,入眼便是魏巍熊耳山,它雄伟挺拔,与天接连,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绵延无穷。自然的生态环境,不光孕育了上百种树木,同时还生长着许多种天然名贵中药材。在祖辈的眼里,大山俨然就是一个聚宝盆。在那生活贫穷困苦的年代,没有人知道,它曾经救活了多少人?农闲时间,人们纷纷上山:寻药,拾柴,砍椽,背杆(建房用地檩条)担炭……风里来,雪里去,磨破了双手双肩,累弯了老腰老腿,卖了换几个零花钱,只夠糊口,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却依然摘不掉头上的那顶穷帽子。
“走出家门天地宽,又学技术又挣钱”。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声声召唤下,我们放下了赖以生存的,扁担绳索,锄头镰刀,走出家门去开辟新的天地,很快我们摘下了穷帽子,走上了小康之路。通过不断地打工,学习,我们至少掌握了一种或多种生活技能,而不再依赖大山生活。
近几年,国家又投巨资在熊耳山大峪沟,赵沟地段,修建河南省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发电站,目前,已经初具规模。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魏巍熊耳,必将以崭新的姿态,震惊世人。在为祖国电力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又能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发展。这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儿吗?真好。
俯瞰,有一条南北转东西流向的小河,从村前流过:它冬春时节,好似玉带缠绕,袅袅渺渺,怡静如一位绝佳少女侧身而卧,那沽沽的流水声,犹如情人喃喃细语,令人如醉如痴。而夏秋时节则是别有一番景致:每次山洪爆发,往往是滚滚波涛伴随着隆隆巨响,浑浊的河水从天而降,一泻千里……那气势,那场面,真是波澜壮阔,令人叹为观止。洪水过后,被激流冲涮出的一个又一个深滩,便成了我们孩童的乐园,洗澡,游泳,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河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石头下面藏着我们童年的梦想和记忆,摸鱼,捉螃蟹,逮老鳖……即使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总是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题。
沿河两岸的田地,比较平坦,修有水渠,便于浇灌,冬春小麦,夏秋玉米。南岸属于我村的只有极少数土地,被分作自留地,用来种菜。北岸的田地不多,那可是老辈眼中的黄金地,天旱时节,更是村里的保命地,可惜后来被批为宅基地,盖了房子,也就是现在的安坡村。
进出安坡村的主要通道是一条乡间公路。从现今教会(这里原来是一片石头荒滩,后院西教会搬迁到此)西拐,过小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那便是洛宁白马寺历代高僧圆寂的地方。记忆中至少有七座石佛宝塔,可惜大都被推倒毁掉了。只留下了三,四座,一座完好,三座不全。如今的佛宝塔更是被列为了县级保护文物。世事无常,谁能想到昔日鼎盛辉煌的寺院,如今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不管是 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安坡村的整体布局像一把太师椅,无疑是适合人住的风水宝地。还是从迷信神学的角度看,有历代高僧的护祐加持。我们安坡都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好地方。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通过在外人士的牵线搭桥,安坡村率先用上了电,第一个使用上钢磨。先后修建了两座跨河桥,一所希望小学(即现在的安坡村委),可以说他们功不可没。我们不仅要记住他们,还要告诉我们的后人,那些为村里建设做过贡献的人,都不应该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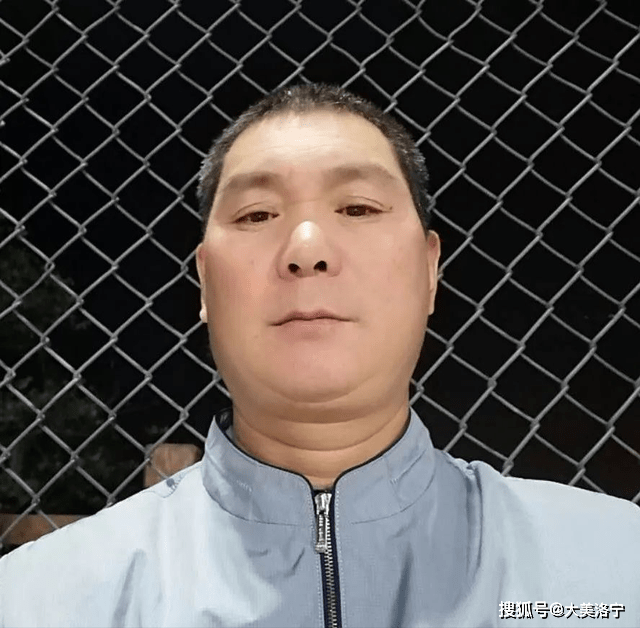
作者简介:杨建涛,洛宁涧口乡安坡人,一生平淡,打工谋生,业余爱好戏曲和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