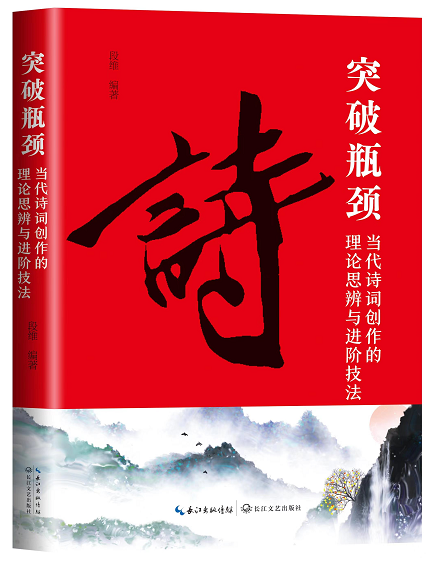
段 维
作诗填词久了,回首过往,如果把诗词从初创、修改到完成看做是“成品”出炉,那么这个过程似乎可以拆解为必经的三个阶段,或者说要过三道关,抑或三道坎,那就是技术、艺术、哲学三个层面。技术层面是指格律、押韵、炼字以及句法章法、逻辑结构运筹等方面。初学者以为格律、押韵最难,其实句法的变化、用字的锤炼都要比格律、押韵难得多。而这些也是诗词出新的最基础的窍门之一。送张子尉之南海
岑 参
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
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
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
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鲛人:本指神话传说中的人鱼,这里指渔夫。宝玉:这里当指唐代风清气正的民风乡俗。
岑参与高适同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掌门人,人称“高岑”。这是一首送友人任南海县(今属广东)尉的诗。开篇嘉之以“孝”,结尾勉之以“廉”。颈联“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既是词类活用(“暗”“明”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又是倒装句,即“三江雨使海面变得暗淡,五岭春让山花显得明媚”。这里十分注意炼字、炼句。我写过一首《远眺武当南岩》的七律,不妨也作为例举:远眺武当南岩
段 维
凌虚高阁生玄妙,香冷龙头动楚吟。
壁吮残阳红透骨,松呼断雁绿操琴。
无为编织游仙梦,大难煎熬济世心。
向使英雄都羽化,山河终古气萧森。
其中颔联“壁吮残阳红透骨,松呼断雁绿操琴”的句法和炼字还是有些特别之处的。这也算是技术层面的。西 施
罗 隐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这首咏史诗以古讽今,意在言外。在结构上运用“层层推理”的方法,最后得出西施不是亡吴的根源,替西施昭雪。这堪称是技术层面的“精构”。有感于“官不聊生”说
段 维
官不聊生造语奇,风从空穴湿人衣。
若为直到穷途处,应有辞呈雪片飞。
这首诗也主要是从结构推演方面着手的。诗中“应有”表达的其实是“没有”之意。这种讲究逻辑推演的构思,主要注重艺术逻辑,不一定是事实逻辑。看下面的例句:此诗开篇即以议论出之,“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典照应国亡之意。晋时索靖有先识远量,预见天下将乱,曾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叹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通过两个并列的镜头,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小怜”即其名)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司马相如语),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今山西太原),向齐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后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诗人将小怜进御与北周的军队攻破晋阳这两件并非同时发生的事,颠倒时空剪接组合在一起(可见艺术真实不一定得抱守历史真实),揭示了北齐当政者荒淫腐败而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既耐人寻味而又发人警醒。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2.艺术层面
艺术层面就是着重于意象、意境的出新。意象就是“意中之象”,是作者主观情意与客观对象的统一体。意境是由一个个相关意象有机组成的,是情景交融的产物。这两方面出新都很难。下面我们分别来剖析一下两种做得不好的情况:
其一,诗词的有“意”无“象”。意就是思想或理念;象就是物象或事象。“意”与“象”的结合,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换言之,意象乃是客观外界的具象(物象或事象)映入诗人的大脑,经过思想或理念的投射得到的产物,简称为“意中之象”。张其俊先生认为,意象可分为单个意象和复合意象。在诗人的笔下,总是先将单个意象组合成若干复合意象(诸如意象叠加、意象密集、意象脱节),也称意象单元,再按照在构思中设定的程序(诸如意象并列、意象组合、意象并列与组合)将这些意象单元整体装配成诗歌艺术成品,也就是形成意境。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有“意”无“象”的诗,诗中全用逻辑思维或理论术语,也就是说以抽象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念,尽管注意了平仄,但却缺少形象,缺少艺术感染力。有“意”无“象”的诗,其语言肯定不是诗的语言。其实,不仅现代人易犯这个毛病,古人甚至是名家大家也不例外。我们看王安石的一首绝句:
“鞅”:其读音查《汉语大字典》有两读。一是《集韵》的於良切,读阳;二是《广韵》的於两切,读养。字典特地标明:“旧读yǎng”。
这首绝句只是以商鞅“立木取信”并兑现承诺为例,说明诚信的重要性。缺乏形象,缺少情景,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意境了。
其二,诗词的有“象”无“意”
另外一种现象则是诗中有“象”无“意”。也即是诗中罗列了许多意象,却没有明确的“意”将其贯串,或者许多“象”相互乖离,与诗中的“意”不搭界、不相融。先看宋杨亿编选的《西昆酬唱集》中他自己的一首七律《泪》:
诗中写了八种“象”——思妇停机、弃妇怨吟、征夫肠断、纤夫闻猿、皇妃冷宫、壮士击壶、士子悲秋、闺人伤春。但相互之间犹如散珠碎片,没有一个明确突出的“意”加以串联。《西昆酬唱集》中这类作品很多,在文学史上屡遭诟病。
我们再看黄庭坚的一首词:
词的上片用三个景象组成绮丽的意境,但一、二句中的“眉黛愁”与“眼波秋”不谐,一“愁”一“媚”,没有关联;上片总体写绮丽之景,与下片则写渔翁的悠闲自在,有飘然出尘之意,与上片也不搭。无怪乎苏东坡开玩笑说:“才出新矶妇,又入女儿浦,此渔父太澜浪也。”(见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归纳来说,诗词中有意无象,不是诗的语言;有象无意,不是诗的章法。两者都不能创设情景交融的意境。
其三,遣词对诗词意象的损益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象”与“意”都好,但遣词造句欠妥,结果使意象打了折扣。我们看谈唐代李端的一首诗:
这首诗世人评价很高。但顾随先生却找出了毛病。(顺便说一下:《顾随诗词讲记》中,原文把该诗的作者误作李白。也许是顾先生口误,也许是叶嘉莹先生所记笔误。后经顾随之子顾之京整理,再经出版社三审,也就是说至少经过六人之手,错误都没有纠正。所以我们不能盲信他人,即使是名家。)对这首《拜新月》诗,顾随先生认为:“拜月真是美事,女儿拜月真是美的修养。每夜拜月,眼见其日渐圆满,心中将是何种感情?”但“开帘见新月,即便下街拜”,写得像李逵,真写坏了。“细语”句尚可,“北风吹裙带”,绝不可用“北风”。这说明,意象的营造考验诗人的综合素养。
大凡优秀的诗作,都是遣词妥帖恰切,将“意”与“像”关联无间,允称妙合。以象达意,意寓象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只举白居易的一首绝句:
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运用了新颖巧妙的比喻,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全篇用“可怜”二字点逗出内心深处的情思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其写景之微妙,历来备受称道。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评云:“诗有丰韵。言残阳铺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红,日所映也。可谓工微入画”。乾隆皇帝在《唐宋诗醇》中评云:“写景奇丽,是一幅着色秋江图”。清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云:“丽绝韵绝,令人神往。”3.哲学层面
哲学层面的问题,起始于“思维”,终达于“境界”。境界不是靠聪明或技巧就能到达的,要靠器识与胸襟,还有思考过程中哲学思维的引领与托举。具体讲如陈永正先生所言之“独立人格,忧患意识,自由思想”,具备了这些,才有可能洞察幽微,胸怀天下。这就难上加难了。不少人精通格律、句法、炼字,也很善于选取意象和营造意境,但所写的东西之所以昙花一现,就是差在境界不够高远上面。
2011年5月末,我去了一趟沈阳,参观故宫时发现牡丹正在怒放,而此时洛阳牡丹早已凋零。于是由此发端,填了一阕《汉宫春·沈阳故宫牡丹》,颇受诗界好评。一位近70岁的秦皇岛诗友,还专门为这首词谱了曲。现录词如下:
国色天香,锁后宫苔砌,烟雨霏微。相扶伫立,玉盏静候谁归?图强霸业,向中原、新画蛾眉。浑未觉、皇冠尘土,猩唇更胜当时。岂是洛中夭艳,俟阳春一去,魄走魂飞。征人梦回故里,肠断何其。翻疑塞北,有贞芳、坚守琼枝。休揣度、名姝心事,风来秀靥迷离。词以“景”起,“相扶”“玉盏”是描摹形态。“图强霸业,向中原、新画蛾眉”,是回答“谁归”句的。“浑未觉、皇冠尘土,猩唇更胜当时”是作者的想象,“猩唇更胜当时”句让人觉得不胜凄凉。过片引起两地牡丹花的对比。“征人梦回故里,肠断何其”,也是推想与想象。“翻疑塞北,有贞芳、坚守琼枝”句将情感推向高潮。结句拉回到眼前。“休揣度、名姝心事”,看起来是否定句,实在是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确定性思考。“风来秀靥迷离”,照应开头,以“景”作结,却有言之不尽之意。上面讲到了诗词创作的三个层次,带有一些抽象意味。那么是不是注意到了这三个层面的东西,写出来的就一定是好诗呢?这个不敢保证。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前面已经提到了叶嘉莹先生的“方法论”表述和杨逸明先生的“效果论”见解。我觉得,还可以从“文本论”角度总结出四个方面:有真情、有高格、有新意、有妙语。这四个方面与前面说的三个层次无法一一对应,但也不是没有关联。比如说,有新意,包括立意新、构思巧,就属于艺术层面;有妙语既有技术因素,更应该属于艺术层面。有高格对应哲学层面。有真情无法对应任何层面,但却是作为“好诗”的基础和前提。缺乏真情,谈其他层面的东西毫无意义。该文节选自段维编著:《突破瓶颈:当代诗词创作的理论思辨与进阶技法》(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第十六讲。另外,为了便于阅读,部分脚注改为文內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