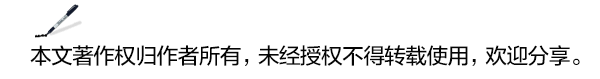硕士研究生毕业,刘德山来到山东医大附院中医科工作,跟着科主任陈克忠教授干中医。时间不长,按照医院规定,他下到重症监护病房(ICU)锻炼,时间是一年。
这天,ICU进来位女病人小周,姑娘患上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部严重感染。经过治疗,她的感染虽被控制住,消化道却反复出血了,输上血,血色素上去,停止输血,血色素掉下来。
按照常规,继续输血,用洛赛克、氢氧化铝凝胶治酸,用凝血酶止血。能用的办法用上,病人呕血、黑便依旧。
刘德山跟科主任商量,能不能用中药治疗,科主任同意了。
刘德山按脉查舌,辨证施治。他说:“我给她选用了三黄泻心汤加减治疗,很简单的几味药:黄连、黄芩、黄柏、大黄加白芨,碾成末冲服。三服药下去,小周出血止住了,大便不黑了。过了不久,小周康复出院了。”
神了。
一年ICU锻炼期很快过去,病房领导希望他留在ICU工作,爱动脑子又勤快的年轻人,哪个领导不喜欢。领导不知道的是,中医已成了刘德山的命,他不能不要命,他回到中医科,继续当他的中医大夫。再后来,医院成立肿瘤中心,有人动员他去那里开疆拓土。他还是以“命”为重,不为所动,吃国库粮的想法离他已经很遥远了。
早在跟随陈克忠读硕士的时候,刘德山认识了在中医科工作的张继东大夫。刘德山回忆:“他刚刚40岁,沉稳儒雅,办事干练。1992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分到中医科,和他接触逐渐多起来。”张继东是《伤寒论》大家徐国仟教授的硕士,1992年,张继东作为全国首批学术继承人,拜中医科主任陈克忠为师。这种机制当时简称“带高徒”。徒弟出师后马上可以晋升职称,是讲师的升副教授,是副教授的升教授,不受名额限制。张继东融中西医于一体,擅长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特别是在运用中医“益气活血”、“补肾活血”等法则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老年冠心病等方面颇有建树。
后来他与刘德山同在中医科工作,二人更为熟络起来。张继东经常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临证体会分享给刘德山。2002年,张继东继陈克中之后成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老师,也开始带高徒了。刘德山抓住机会,拜在张继东门下,成为他的高徒。如此一来,在齐鲁医院中医科里,师徒关系变得有趣起来,刘德山是陈克忠的硕士,张继东是陈克忠的高徒,刘德山又是张继东的高徒。1997年张继东接替陈克忠担任中医科主任,2010年刘德山接替张继东担任科主任。
这天上午,笔者悄悄溜进刘德山的诊室。
诊室坐东朝西,屋里两张小桌,一张检查床,外加两个金属橱子、几把方凳。小桌一张放在一进门的地方,供学生写病历;另一张放里边冲门的地方,供刘德山诊病开方和学生抄方。
就诊的、待诊的、陪诊的,加上侍诊的三位研究生,刘德山陷在“包围圈”里,连转身都困难。
病人有个人来的,有夫妻同来的,也有两代三口人一起来的。
他们常常是一人吃了药见好,一家人都来了。
镜头一:
今天写病历的是研究生小刘,他坐在诊室门口。
我问小刘:“刘主任看病有什么特点?”
小刘说:“医术高,态度好。”
回答简洁,加上标点,一共八字,好像考试做填空似的。
“德取谦和善如水,医臻精妙情如山”。
诊室左边墙上挂的镜框里,镶着一幅嵌字对联,像是给刘德山画了一幅肖像,病人对他的评价与感激都在里边了。
“你的脉象好多了。”
刘德山搭着脉,给病人打招呼。
“我感觉能吃上饭了。”
“能吃饭好啊,我给你再调调。”
诊室里的病人都感觉得到,刘主任的笑意穿透了口罩。
“啊,来啦!”
直到我拿出手机拍照,他才发现采访的人到了。
春天的气温总爱上蹿下跳,那天赶上上窜,腋下生风的雅事不会发生,腋下生出来的全是汗液。
面对纷纷拥拥的病号,大夫虽然累,心情不会坏到哪里去,谁都知道,诊室就是票箱,病人在用双脚投票。
刘德山得“票”高,年门诊量5000多人。
这么大量,当大夫的只要走心,练也练出来了。
镜头二:
淄博来的小宋过来坐下,刘德山一边搭脉一边问:
“哪里不好?”
“干咳,过敏性鼻炎,还特别好着急。”
“抽烟吗?”
“抽。”
“以后戒了吧。”
“争取,我现在就是有痰咳不上来。”
趁着开方,小宋告诉我,自己患过敏性鼻炎多年,在淄博老家做过两次手术,效果并不好。刘德山掏出手机让他手机扫码,有问题网上解答。我问他小宋病在哪里?他说是肝气犯肺。
接着坐下的,是小宋母亲徐女士,她与丈夫、儿子今早4点多从淄博坐长途赶来的。她说自己是刘主任的老病号,找他看病已经三年。儿子现在广东,回一趟山东不容易,索性一块过来看看病。在一旁的老伴给刘德山提建议说:网上挂号最好一次挂两周,你的号太难挂了。
刘德山忙解释:“网上只能挂一周,这是医院规定的,为的是限制网上的号,不然很多老年人网上挂不了,对医院就有意见了。”
“是啊,”护士小黄插话道:“前几天,有位老人打电话到济南市政务热线12345投诉,反映挂不上刘教授的号。”
镜头三:
小张姑娘坐下了,她指着额头,说:“刘主任你看,吃你的药,两个大疙瘩下去了,睡觉也好多了。”刘德山搭脉看罢舌象,对她说:“你还有点阴虚内热。”站一旁的丈夫连忙打趣:“对,刘主任,你给她打打火。”小张轻拍他一下,扭头娇嗔道:“不用你多嘴。”
来看病的老年病人多为癌症患者,经刘德山辨证,他们几乎个个虚实夹杂。
这位女患者姓孙,70岁了,患直肠癌,动过手术,这回来看的是气管炎。这位女患者姓徐,患的也是直肠癌,动过手术,最近胃胀,吃东西没有胃口,想找刘主任给调一调。
镜头四:
茅先生坐下了,他今年72岁,腰板挺直,面色红润,除了反应迟钝些,外表看不出什么病态。刘德山侧头轻声告诉我,他患血管性痴呆。
刘德山搭上脉,笑眯眯地说:“老爷子你的脉好多了。”
老伴告诉笔者,丈夫三年前得了中风,由于耽误了治疗时间,老头睁不开眼,说不了话,也不能吃饭,体重降到了92斤,中间还走失过好几次。
“经过刘主任治疗,现在能吃饭了,体重快140斤啦,你看精神头好多了。”
她边说边学老伴当年的样子:“三年前他就这样”,她向右侧弯腰弓背,身体下弯90度,“你看他就这个样。”
她一边学,一边讲述三年前就诊时的遭遇:
他们找到某某专家看。专家说来晚了,没法看了。
“照你这个说法,俺老头不等于判了死刑了吗?”
大概都在气头上,谁也没有把住门,专家的火也上来了:“对,判了死刑啦,谁让现在才来……”
听说中医有办法,他们就挂了刘德山的号,结果老人的病眼看着见轻。
老伴看完了,现在该她了。
她姓温,患的是子宫癌,她说找刘主任看病三年了,越看越好。问咋个好法,她说过去下肢疼,从腿疼到脚,现在不疼了,脚凉的毛病基本没了,剩下的就是脚心还有一点问题,老人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寸面积,脚心这么大的地方还有点凉。
“这还算个病?”
“有好大夫在这里,能看就看嘛。”
她真想开了。
镜头五:
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一位老年病人靠过来搭话,他说自己患的是食道癌,手术后吃不进东西,吃了刘主任的药,很快就能吃饭了。“刘主任算是把我救回来了。我过去颈椎也不好,胳膊一直麻,吃了刘主任的药全都改善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看脸上疙瘩的,看咳嗽上不来痰的,看颈椎病的,看癌症的,看脚心凉的,给人感觉老中医的传统又回来了。
“你是个全科啊?”我说。
“嘿嘿,我就是个全科啊。”
“全科好啊,中医大大夫没有不是全科出来的!”
但是,假如大夫没有拿手好戏,就是一盒万金油,哪里都能膏,哪里都不突出,到老也成不了大大夫。
中国人看中医,常说吃谁的药,找王新陆看,就说吃王新陆的药,找王新陆的徒弟刘德山看,就说吃刘德山的药。谁的药被吃的多,谁就是好大夫、大大夫。中药房里药橱满墙,装药的抽屉,人称药斗子,药斗子里装着中药百味。中药房要是有人的思维,一定郁闷得很:一屋中药怎么成了大夫的药呢?道理不用多讲,每位中医心中都有数不清的药斗子,组方配伍,全在他心里。中药房郁闷不着。
有位患糖尿病肾病的病人,尿里大量泡沫,来到齐鲁医院中医科求治。刘德山接过化验单一看,病人尿微量蛋白超过了1800mg/L。正常人尿里是没有蛋白的。此前他找西医看过,经过次治疗,尿蛋白没降多少,西医大夫只好告诉病人,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病人吃刘德山的药仅仅一个月,病人尿微量蛋白降到了200mg/L以内。病人把结果告诉给他看过病的西医大夫,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要求病人再化验一次。再次化验,患者的蛋白尿还是在200mg/L以内,这下他们服了。
经过近三十年的临床,无论化裁经方,还是妙用时方,刘德山辨证遣方越来越得心应手。
吃饭、吃药。
走出诊室,不知怎的,这四个字总也挥之不去。
老话讲,民以食为天。中医讲,五谷为养。全世界的文字中,恐怕没有比中文“吃饭”的意思更多的了。
在哪里吃饭?问的是哪里工作。
工具丢了,常说吃饭的家伙找不到了。
今天真出奇了:
正写到“吃饭”,手机里传来噩耗:时年91岁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院士不幸辞世!
“一定要把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悲痛之余,想起老院士最有名的那句话。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一生,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他与他的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正在美国、印度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推广,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靠种植超级稻吃上了饱饭。
老院士,愿您在天之灵安息!
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活着,离不开吃饭。
这是常识,也是公理。
人得了癌,开刀还是不开?
开的,不开的,都有成功的,也都有失败的,也都有典型病例。开的,不开的,吃饭都不好。
对晚期肿瘤的治疗,刘德山极力主张“带瘤生存”。他跟很多人介绍过,医生治病是不让人体长坏细胞,或让坏细胞变成正常细胞。就像警察抓坏人一样,防止坏人变成危害社会的黑恶势力,就维系住了社会的平衡。保持阴阳的平衡,代谢的平衡,在西医上叫做保持稳态,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和合思想。
他怕我不明白,继续解释道:“老年癌症患者,不像年轻患者,凡是来看中医的,大都是经过化疗、放疗后来的,他们阴阳失调,气虚脾虚,虚实夹杂,吃饭没一个好的。病人初诊,有坐轮椅来的,有被搀着来的。几副药下去,病人自己来了。他们吃上饭了,睡着觉了,治病有信心了,人生也有信心了。”
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刘德山学术观点是“治虚先健脾,健脾必益气”。从脾胃入手治病,医学界代不乏人,易水学派代表医家李杲著有《脾胃论》,其观点为:“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现代名医蒲辅周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健脾不就是让病人脾胃好,能吃上饭吗?病人吃饭有胃口了,病不是才好得快吗?
中医治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通过大夫的调理,谁能让病人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对生活重拾信心,谁就是好大夫。
刘德山已经成为这样的好大夫。
他看病看得好,科研成果也毫不含糊。这一二十年来,他主持省级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10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主编参编著作6部,发表论文150篇,其中SCI、EI论文18篇。
“恕我问句冒昧的话。”
第一次采访结束前,我这样问道。
“请问。”
“你的中医干到今天,你感到自己的不足在哪里?”
“老师告诉我,学中医有三个层次,一是学会,二是精通,三是化境。我认为我还不够精通。中医博大精深,真正学懂弄通,达到融会贯通不容易,我必须加倍努力,继续学习。现在好多中医存在的问题是,他们知道什么病用什么方,但为什么用这个方,还是说不清楚。所以有人说,西医是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糊里糊涂地活。”
这是刘德山的谦虚,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的清醒。
他的希望正在这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