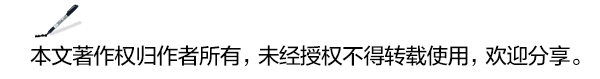山东医科大学是卫生部部属院校,其前身是齐鲁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的前身,是外国教会办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和后来的齐鲁大学医科。民国时代,“南有湘雅、北有齐鲁”,的说法可不是广告词,教学实力在那里摆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停办,齐鲁大学医学院改名山东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后来合校,并入山东大学。
1984年之秋,刘德山走进山东医科大学。
这是山东最美的校园,古树参天,花木扶疏,中西合璧的教学楼古朴典雅,一座座掩映在绿色的林荫里,是个读书再好没有的地方。与所有的新生一样,刘德山进了校门就爱上了母校。
最让刘德山着迷的是学校图书馆。这所图书馆的前身是齐鲁大学奥古斯丁图书馆。1903年,山东省内的三个教会医学学校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各校的藏书一并划入。1922年,加拿大危培革奥古斯丁长老会支会捐赠巨款修建的奥古斯丁图书馆投入使用。还是在1922年,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桂质柏先生担任了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到了1930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建立,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这里一度成为全国国学研究重地。齐鲁大学响应“整理国故”的大势,利用美国霍尔基金赞助,成为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教育与研究计划的六所教会大学之一,一次获得15万美元专项经费。这在当时是个天价。据齐鲁大学1936年6月统计,图书馆馆藏已达11.8万余册。1937年藏书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2万册,其中大部分为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经费购得。这是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量最丰富的时期。后来院系调整,有些文科书被调剂到当时的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但是医书还是屡有置办。
不能白来这么好的学校,不能辜负这么好的图书馆。
刘德山发愤了。
在学子们眼里,图书馆有一种征服心灵的魔力,它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刘德山是从家乡水“汪”里游过来的一条小鱼,游到这里,小鱼明白了什么是大海,什么是大海的汪洋恣肆。他明白,要想在大海里遨游,自己会的那点狗刨肯定是不行了。要学到真本事,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刘德山一直是图书馆的常客,平日他总爱泡在图书的海洋里,一心想把自己练成劈波斩浪的游泳健将。
刘德山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空前解放,数学家陈景润成为一代人的偶像,人人知道他研究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女排崛起于世界,民族自豪感被极大唤起,振兴中华的呐喊融进彼此的血液。各种科学新知纷至沓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来了,生物医学模式进来了,《大趋势》《未来的冲击》未来学著作进来了。有的新学科开了课,像医学心理学,有的图书馆里有,想读什么有什么。钱学森关于生命科学的书籍和论文,他读得蛮有滋味,气功书他也读过几本。
对系统论、控制论这两门新知,刘德山读得最有心得。比如系统科学与控制科学,对世界科学及工程科学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传到中国时已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通过学习,他明白了系统科学有三个要素,即整体、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整体不能脱离要素而存在,要素与要素相关联,影响着整体,要素相加不等于整体。这些观点与哲学重点论与两点论的关系,以及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事物,与中医看病讲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何其相似乃尔!
再说控制论。在对事物控制时,控制论要求尽量缩小可能性空间。比如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患者,医生先治哪种病,心中需有整体大思路,好医生会根据病人病程,或下药直达病灶,或迂回下药,变化之妙,存乎一心。好比两国交兵,聪明的一方会千方百计,促敌由强变弱,压缩敌方对己方进攻、包围、偷袭的可能性空间。用控制科学的话,治病的过程就是控制的过程,就是缩小多种疾病可能性空间的过程。
读书读到这一步,刘德山算是读开了窍。
笔者见过一幅齐鲁大学医科的老照片,上面是民国初年学校的解剖教学课,照片上八九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其中还有两位端庄清秀的女性,他们盯着一具尸体,听西洋老师讲解剖课。历史穿越百年,给人一种无声的震撼。
一个世纪过后,刘德山接过解剖刀,用那双掏过鸟窝抓过鱼的手解剖尸体了。他延续着高中时的神话,各科成绩遥遥领先,解剖学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周围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不过,也有异样的眼神,也有不解的笑声。
你学习好,当然好;你读书多,我们佩服;你在图书馆里一坐一天,追求新知手不释卷,大家也服气。可一个学西医的,整天抱着《内经》《周易》啃得入迷,所为何来呢?
我问刘德山:“在一所著名西医院校攻读西医,同时自学中医,西医听诊化验、抗菌消炎,中医四诊八纲、清热解毒,体系不同,概念迥异,这就像一个学歌德、莎士比亚的,课余时间换成李白、杜甫,你能换得过来吗?”
“换得过来。”
刘德山笑眯眯地说。
“越学新东西,越觉得中医科学。比如说,现在已有报道,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有了心脏供体人的思维。中医早就有‘心主神明’的观点,你说科学不科学?”
“老师和同学能理解吗?”
“当然不会都理解。”
“怎么个不理解法?”
“有同学喊我老中医啊,哈哈!”
话语很有画面感:
同学们正在一块说笑,看见刘德山过来,有人打趣:老中医来了。
在中国人语境里,“老中医”是个尊称,意味着大夫的资望、水平跟名气,而刘德山耳朵里的“老中医”,像是撒上了一层咖喱粉,有一种异样的气息。
刘德山懒得解释,他明白同学这样称呼,虽有点不太理解的成分,总归是友好的戏谑,而非恶意的揶揄。
刘德山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医院里到处是老同学。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老同学经常向“老中医”推荐病号,病号里不乏同学们的亲戚朋友。
医院不是科研院所,不管中医还是西医,病人只认疗效,疗效是硬道理。就像战争时期打仗、和平时期建设一样,谁的办法能打赢听谁的,谁的办法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裕听谁的,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邓小平找到改革开放之路。对病人来说,谁的药吃着好就找谁看。
刘德山明白,老中医得熬,不熬,出不来老中医,可是话说回来,哪一位中医熬白胡子,不都是老中医吗?有些中医熬到了年头,诊室不也是门可罗雀吗?真正名老中医,美名响四方,靠的是临证明辨阴阳,下药效如桴鼓。海尔总裁张瑞敏说过,名牌产品不是评出来的,卖得快卖得贵的产品才是名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