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旅程。生命不停地飘移,飘得远了,中途不能没有歇息之所。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述:“曲曲折折的路旁,隐现着几多驿站,是行客们休止的地方”。
于我而言,几十年走来,老家的县城、距县城几十公里的江边码头,直至参加工作之后经常出差,偶尔外出旅游等等,驻足过无数驿站,它们都曾给我的身心有过些许的放松,留下过些许的宁静、清凉或温暖,但它们仿佛只是一个个住宿和行止的符号,留下的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真正贯穿始终、几十年如一日,既给我途中歇息提供方便,也给我以回家感觉的,只有一个地方——大妹妹的家。
那是我回家和外出途中住得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大妹的家处在一个傍河的集镇。一条大河自北向南纵穿而过,河的上游岸边曾有一条老街,与我读高中的母校隔河相望,后来河被拉直,老街远离河岸,生意逐渐萧条,老街的房屋和店铺陆续迁徙到下游河岸的新街,大妹的家就在新街。
从我出生的村庄来到这里,虽然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但一路翻山越岭,走了一大半山路之后,方见豁然开朗,接上宽阔的公路。于是总觉得路远,尤其是集镇对面的绵绵群山,它远远高过我家村庄附近的许多丘陵;站在街口望去,群山好似扑面而来,又像遥不可及;它时而油光叠翠,与蓝天相接;时而苍烟若浮,云蒸蔼蔼,令人悠然恍惚。当年我在集镇附近的高中读书时,多少次坐在河边,俯瞰河水里远山的倒影,把在水里漂浮的云朵想象为奔驰的蜡象、温柔的绵羊,想象成白衣仙女的翩翩舞姿。忽然阵阵清风吹拂,远山的雾气弥漫开来,河水顿时显得混沌,似把这天国的景象,悄然推向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我离开家乡四十余年,山水沧桑,世事茫茫。不断变化的是家乡的田野和村庄、房屋和道路,路上不断增多的陌生面孔;不变的仍旧是,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的记忆、期盼与与梦想。
我离家不久的那些年,城乡交通不便,回家或去省城何处搭车?搭车去县城后,能否赶上唯一的一趟去省城的长途客车?若赶不上这趟客车,将在何处栖息一晚?如此纠结,一直颇费思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妹妹成家以后,在集镇上有了她自己的住房,我旅途无处落脚的困扰终于解脱——去她家落脚片刻或一晚,在集镇车站搭车外出或回家,实在方便多了。
把大妹的家作为旅途驿站,不仅有我,还有其余兄弟姊妹,包括兄弟姊妹的孩子。只要外出或回家,打工也好,读书也罢,在她家落脚只图方便,没有任何商量,不讲任何理由。如果一定要有商量,必需什么理由,那就不符合妹妹和妹夫为人处事的风格。她两口子言语都很短,短到只有见面的第一句问候:“大哥你回来了?”伸手接过我的行李,递上一杯热茶,让我落座之后,就等着我一句一句地询问他们:家里可好?工作忙吗?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我不主动发问,交谈就此打住,屋里只剩下他们忙进忙出的身影,一个忙着为我准备饭菜,一个急着为我整理房间和铺床;一大桌荤素菜肴摆上餐桌之后,他们终于开口,不停地劝我多吃,你吃得越多他们就越高兴。饭后,妹夫默默地陪我到街上转悠,所见所闻,依然是我问一句他答一两句。睡觉之前,妹妹从楼下厨房里提来几个开水瓶,那是她为我提前准备好的热水,要我上床之前好好洗脸泡脚。第二天临走时,大包小包的蔬菜、鸡蛋、红薯、山药之类土特产品随我上车,回头望去,妹妹和妹夫默默站在门口,目送着我的车拐过街角,呼啸远行……

几十年来,这样的经历不计其数。问及其余兄弟姊妹,待遇也都差不多,尤其是他们的孩子—— 我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们,对他们而言,大姑(大姨)的家虽然离自己的家不远,但回家或外出时,如不到此停留一刻,似乎就缺少点什么;殊不知,这里是他们离家和到家时必经的驿站。特别是我,父母亲相继离世以后,其余兄弟姊妹常年在外,大妹的家,就成了我回老家时唯一的去处,这里既是临家的驿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家。
虽然大妹性格内向,从不多言,但是令我意外的是,母亲离世的那天晚上,大弟正在与我通电话、告知噩耗时,电话的另一端,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丧声,句句都是母亲生前对儿女们如何如何的好,是她和姊妹们对老人家的不舍和怀念。我听着似很熟悉,又很陌生,问了弟弟才知道,那是大妹在哭。我顿时感到震撼,一个平时言语如此短少的人,她心中的闸门开泄之后,竟是这样地汹涌澎拜!
从此以后,我每年清明必须回家,必须在大妹的家里歇息一至两天。一是为了祭拜父母等逝去的先辈,二是与妹妹一家团聚;交谈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几句简单的问候,抱抱她的孙子,也是难得的温情和享受。每次来到父母的坟前,在燃放鞭炮,鞠躬默哀的那一刻,妹妹总是对着墓碑窃窃私语:“爹啊娘啊,你们听到了吗?大哥回来看你们了;你们如有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兄弟姊妹幸福平安吧!”没想到,平时话语不多的妹妹,竟然也有如此唠叨的时候。
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有话就随时接通对方的时代,除非有事,大妹与我、与其余兄弟姊妹,照例很少互通电话,但并不因此相互计较,因为我们已经默认,她的家就是我们这些“行客”们的住所,我们随时可以到她那里歇息、用餐,让她倾听我们在外奔波的喜怒哀乐。到达她的这个驿站之前,我们既可以事先通知,也可以不打招呼,径直闯入。这种不讲任何礼节的习惯,可以一直追溯到几十年前,那个很少电话、没有微信和短信,只有纸质媒介通讯的年代——
那是一个凉风习习的深秋,大妹帮舅舅带了几个月孩子后,从河南某部队回家,途经武汉时,我领着她在长江大桥、武昌司门口、汉口六渡桥、汉阳归元寺等处玩了几天以后,送她到汉口码头乘船回鄂东老家。计划让她在鄂东江段的蕲州码头上岸,然后去我大弟弟工作的一个煤矿。与大弟见面后,再转乘长途汽车到县城,在县城乘车回到老家所在的乡镇,也就是大妹现在所住的集镇,随后步行回家。
夜雾蒙蒙,灯光闪烁;汉口沿江码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在港务局售票处买好船票后,带着大妹挤进浩浩汤汤的船客队伍,一步一歪地踏上摇摇晃晃的趸船甲板。在即将上船的那几分钟,一再叮嘱她记住轮船靠岸的码头名称,注意船上广播通知,千万别错过必须下船的蕲州码头;并叮嘱她一路注意安全,回去后及时给我来信,告知平安。
接着就是等待,等她到家的消息。整整一周,不,整整半个月,我日思夜盼,忐忑不安,一直不见她的来信,于是担心她是否上错码头,甚至怀疑她是否被坏人拐骗。正在我万分焦急之时,突然接到弟弟来信,告知妹妹已经到家;接到弟弟来信的第二天,大妹的来信接踵而至。或许是邮寄中途的原因,她的信件竟然在路上走了半个多月之久!
现如今,信息传递速度如此之快,一至两秒钟之际,弹指之间,亲人和朋友即可交流对话,可是,为了不轻易打扰对方平静的生活,为了顾及她那不善多言的个性特征,为了尊重她和丈夫已有的处事习惯,有时也为了一个惊喜,我和其余弟妹只好忍着;实在无法忍耐时,只有“主动出击”,与她联系一下,尽量保持着我们与她、与那个临家的驿站的信息畅通。
然而,大家毕竟不在一起;只有回家,只有来到临家的驿站,我们才能更直接地彼此了解,知道各自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也只有这样,回家的心情才更迫切,更希望在这个驿站停留,享受彼此更多的体贴、关怀和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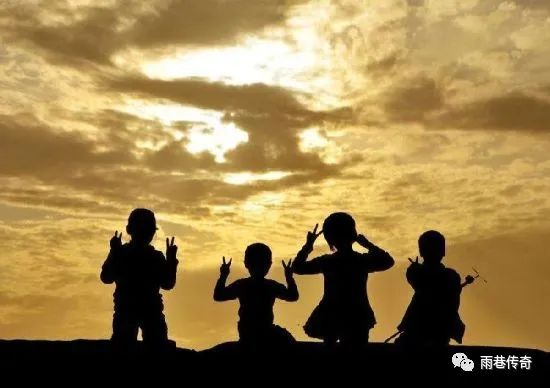
(2021年8月10日于鄂西苏马荡 . 林海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