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没有在家里过年了,如今提及,关于年的记忆倒也零零散散地逐渐清晰起来了。
小时候每到腊月,便开始进入过年的相关准备程序中,每年的这一个月也是家里少有的闲暇又忙碌的相聚时光。
母亲将印经文和雕挂笺的印版刻好后,便安排小姐姐和我印经文,两个外甥女帮着铺纸、晾晒和整理我们印好的经文。姐姐们在准备好食物、窗花、灯笼、年画后,便同母亲一起刻挂笺。
雕刻挂笺对人的精细程度要求颇高,一不小心多雕一刀或者少刻一笔,都会改变其中的字形与画风。所以每每进行到这一程序的时候,偌大的房间总是极为静谧的,舒心的经文静静地颂唱,轻轻的刻刀声偶有间杂。
待挂笺全部刻好后,便到小年了。
所有房间院落一一清洁洒扫后,除夕也悄然临近了。

每到除夕的前一天,父亲便不会出门了。用过早饭之后,母亲清理出家里的八仙桌,父亲便开始润笔研墨。母亲取来准备好的彩色宣纸,父亲一边反复润着毛笔,一边指挥小姐姐和我剪裁纸张。
待所需纸张一一按照相关规格尺寸裁好后,父亲率先着手在大小不一的红色纸张上写下福字。我和小姐姐便托着下巴拄在桌子边上认真数着写好几张大幅字又写好几张小幅字了。父亲每写好一个福字,便会给我们讲解这张福字要贴在何处?寓意为何?
小姐姐边认真听着边揣摩着,总是要问几个问题的。比如这个贴在大门上的福字为什么要这么大呀?那个小幅字为什么不可以倒着贴呀?父亲不厌其烦地笑眯眯地一一耐心解答,我安静地趴在小姐姐身边,思绪随着她的提问和父亲的回答游走。
两个外甥女蹦蹦跳跳地一遍又一遍跑过来问“可是写好了吗?”见我摇着头,便又跑开了。
待福字写好后,父亲便拿过剪裁好的彩色条形宣纸,着手写条幅。那个时候,总是惊讶于父亲不假思索便能一气呵成地写出那么多条幅来。偶尔地,母亲和姐姐们也会道出几句供父亲参考。小姐姐见了便也不甘示弱地背出一些往年的条幅内容来。父亲听了,便会开怀大笑。
我很崇拜小姐姐超强的记忆力,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学霸”这个词汇,不过当年的小姐姐确实可谓学霸了。若是夸张着说,用“过目不忘”来形容也不是很过分的。
福字和条幅都写好后,余下的便是大大小小的门对了。每一道门的寓意与风格皆略有不同,父亲总要斟酌权衡一会的。每每落笔前,都要和大家商讨一番,最终由大家定夺后才会提笔书写。
待上联和下联摆放好后,父亲会潜着笑意问我写何横批才合适?我那时候有八九岁的光景吧,总是要冥思苦想一阵子的。小姐姐便会在一旁急道:“家和万事兴就好,书里就是这么写的。”我小声说道: “合乐安康可好?”父亲也不作答,大笔一挥,“合乐安康”跃然于纸上。
除夕当天的清晨,母亲早早便叫我们起床。为了博得一个好彩头,大家都不会在这一天赖床的。新衣服早已在昨晚休息前准备好,放在了自己的枕头边上。所以醒来,入眼的便是一片新色。伸手拿过来,总是暖暖的。母亲早早起来把我们的衣物提前烤暖和了,为的便是免去我们凉衣上身之苦。
我很喜欢那件毛线织成的素色坎肩,套在衬衣外面既暖和又好看,那是二姐熬夜赶在过年前为我织好的。因为我比较瘦,所以搭配起母亲亲手为我们缝制的长裤来,两条腿看起来会更细,四姐和小姐姐总是会笑我这双腿堪比竹竿。三姐边任由着我们几个疯闹,边拿过来母亲早早为我们用钩针钩好的头花之类的小物件,帮我们打理装扮。
待我们收拾妥当时,父亲已清洁好庭院归来。笑呵呵地入得厅堂来,说话间还带着雾蒙蒙的凉气。我和小姐姐见了,便也效仿着跑到院子里,吸了凉气再奔回屋子里吐出来,当时觉得好玩极了。穿梭在整洁的屋里无外,一吸一呼,一吐一纳间甚是气爽神清。
吃过早饭后,母亲带着二姐和三姐去打浆糊。父亲则召唤四姐、小姐姐和我拿出雕刻好的挂笺和写好的条幅门对等,指导我们如何搭配。一般情况下,一个横批下要搭配三张挂笺。有的时候,若是挂笺所剩不多,四姐和小姐姐便会拣着不属于大门或正门的小角门少配一张。
待做好了浆糊,盛在陶瓷盆里后。三姐总是要过来叮嘱:“可要小心着不要碰洒了!”我和小姐姐每每见了,总是要讨论一番,这个浆糊可不可以当作疙瘩汤来吃?母亲听了,便会笑着告诫,这个是万不可以吃的。
若是赶上四叔家的六哥和二伯父家的七哥来串门,六哥便会大声起哄“能、能吃的!能、能吃的!不、不、不信,你、你们尝、尝、尝一尝!”四姐听了,便默默地踱着步子过来。还没等开口说话,六哥察觉到了四姐的气息,便立刻噤声跳开了。三姐见了总是会与二姐对视一眼,摇头笑上一番的。
六哥与小姐姐年龄相仿,天生有些口吃,所以平时说话比较慢,并且一句话要反复重复几个字才能表达完整。不过,他唱起歌来却一点也不口吃。因此,每每听他叙述一件事情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小姐姐便会着急地在一旁提醒他可以唱着说。姐姐们听了,便大笑起来。六哥也会附和着大笑,果真就唱了起来,口吃霎时间全然没了踪迹了。
六哥时常会和七哥一起来串门,一进屋来,便有笑话可讲,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七哥则静静地跟在六哥身边,时不时地笑上几声,便不多言语了。
由于我天生不沾荤腥,所以平常日子里二伯父总是会在火盆里悄悄埋两个土豆,待烤熟后用牛皮纸裹着包好,让七哥藏到大衣里给我送过来。虽然途经了一段路,但是拿到手里还是热乎乎的。拔掉黑黑的皮,用手轻轻一掰,便露出白中微微泛黄的瓤来。入口松松软软,甚是好吃。
玩笑间,浆糊也凉得差不多了,母亲安排大家首先把条幅贴好。我和小姐姐跟在三姐和四姐的身后,帮着拿条幅和浆糊。三姐和四姐每每在把条幅贴到墙上之前,总是要比对一番的。力求做到颜色不一,又错落有致,甚至连倾斜度都严格把控。六哥对这些向来是不感兴趣的,笑闹一番便同七哥去别处闲逛了。
条幅贴好后,其次便是贴门对了。父亲担心我们贴错了门或是贴反了对子,所以会亲自监督的。
最后,便是贴福字了。从小到大,各处的福字一一贴好后。在贴最后一道大门上的福字之前,父亲要确认大姐和两个外甥女已走出大门去奶奶家过年了之后,才会着手抹浆糊,端端正正地贴好大大的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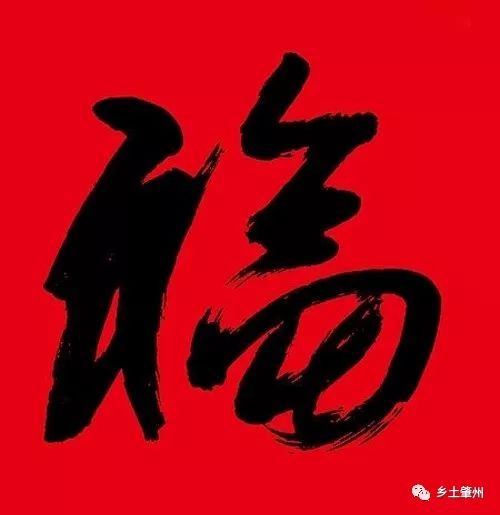
待中间的福字贴好后,邻里亲戚间来串门是可以的。但是,不可借用东西,更不可以再把任何物品带出这扇门了。风俗上来讲,是担心带走了自家的好运气。
贴好条幅、门对和福字之后,姐姐们便随母亲去厨房准备午饭了,小姐姐一定会躲到哪里看书去。我便坐在阶前的木凳上看着满院的条幅发呆,父亲得了闲,也会走过来给我讲解各个对子的含义。我总是很认真地听,并且很感兴趣。
时而听见小姐姐询问我于何处,不待我回应,便会听到她们笑道“莫不是又在发呆了吧?”
每年这一天的午饭总是丰盛而又隆重的,放过鞭炮之后,一家人方可回屋开饭。大家依序坐好之后,要等父亲动了第一筷子,母亲才会夹菜给小姐姐和我,姐姐们随后纷纷拿起筷子夹起离自己最近的一盘。
家里用餐的规矩是不许说话不许剩菜剩饭的,所以那般大的屋子,那般多的人,却鲜少听见杯盘相碰的声音。大家都静静地享用自己近前的餐食,母亲会不时地更换一下各个菜盘的位置。
父亲率先吃好离桌后,大家自觉吃光碗里的食物,把盘中的菜都吃完之后,才起身一起收拾餐盘,清洗碗筷。
我和小姐姐负责摆放桌椅,清洁地面。待打扫干净后,父亲已经沏好了一大壶茶。大家各自喝了茶后,便散去歇息了。
难得的不为生计而忙的一天,母亲会在短暂的休息后,拿过诗词选,坐在桌旁临摹。姐姐们也手里拿着书,入神品读。我和小姐姐午睡醒来后见了,便也拿本书静静地坐在一旁翻看。
记忆中,我和小姐姐总是喜欢同看一本书。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
父亲酷爱看书,除了历史、人物传记之类外,便是武侠小说。他习惯在午睡前看一会,把书压到枕头下面后侧身午睡。
有一次,父亲压放在枕头下面的那本书,恰好是小姐姐没有偷看完的。因为父亲拿去看了,她自是不敢要回来的,所以急得团团转。终于等到父亲睡着了,把书放在枕头下面之后,她便拉着我一起去偷书。
我们两个轻手轻脚地挪进父亲的房间,移到父亲的床前,悄悄地蹲到父亲枕头的位置,静静地等待父亲一个睡姿累了之后翻身。终于在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才翻了一下身,侧身背对着我们的方向。这时候,小姐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两个手指勾到了枕头底下漏出来的书的一角。
接下来,我们继续屏住呼吸,尽量不出声响地等待父亲再次翻身。终于,在腿脚明显发麻之际,父亲又翻了一下身。小姐姐便立刻加重了手中的力道,把书向枕头外面扯了一下。当抬起头发现父亲侧身正对着我们的方向时,我俩险些惊叫出声。急忙蹲趴到地面上,唯恐被父亲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这时抬起头,便能看见书的小半部分都悬空在床外,因为有枕头压着才不曾掉落下来。但是由于父亲此刻的睡姿是正对着我们的方向的,所以我们是不敢继续行动的。
不知又过了多久,才终于听见父亲再次翻身的声音,小姐姐便壮着胆子用手捏住书的一角用力地向下一扯。这时候,父亲的鼾声突然停止了。我们担心父亲已经醒来,紧张得不得了,保持着蹲趴在地面的姿势不敢动,小姐姐的一只手依然紧紧攥住书角。
终于过了几秒钟之后,父亲的鼾声继续响起。小姐姐才轻轻地把书余下的一小部分从枕头下面一点一点地抽了出来。当我们终于把书拿到手之后,自是欣喜与惊恐交加的。不约而同地捂着胸口,轻轻地出了一口长气。
小姐姐看书有一个特点,便是喜欢先翻看结局,然后再翻到前面有针对性地查找她没有从结局里看到的情节。觉得哪一部分有意思了,便又会跳跃到那一章细看。待到把感兴趣的章节都浏览过一遍之后,这本书便算看完了。由于她这种走马观花似的看书方式,所以每每我只需等不多时便可以轮到看这本书了。
后来每每回想起午饭后的那段慵懒又安逸的时光,总是会想起陶渊明的诗句来。我想:“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便是此般景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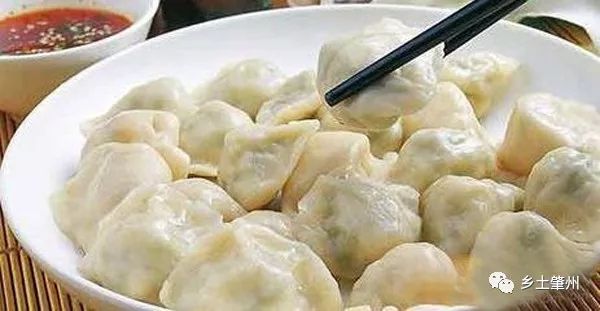
大概到晚上八点钟左右,母亲便叫姐姐们一起动手和面拌饺子馅备用。四姐会提前清洗好几个硬币,小心翼翼地藏到馅料中间,生怕在饺子皮外看出硬币的轮廓来。
每年总是父亲和四姐能够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大家便笑着恭贺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大发财之类的。小姐姐为了能够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总是会多吃好些。屡吃不见之后,便会细细研究饺子的外形,猜测哪个是藏着硬币的。倒也有那么一两次,被她猜中的,每每吃到了,便会开心好久。
大家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父亲会叫上我去庭院东侧的仓房里抱出一些生火要用的芝麻杆一类的引柴来。选出院子当中的空地,层层摆放好后,父亲便把要燃放的鞭炮绑在高高的圆木上,立于柴堆旁。周围零星摆放着几桶烟花和爆竹。
到晚上十一点多子时刚过,父亲便会引燃鞭炮,噼里啪啦的鸣爆中,大家是要捂着耳朵并微微张着嘴的,母亲说这样会防止鞭炮的响声震坏耳膜。

放过鞭炮后,姐姐们便随母亲回房忙碌年夜饭。我则被父亲叫去,走向院落的各个方位,摆放好经文纸,虔心地点燃祭拜。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表情总是肃穆的,我随其左右,亦是不敢言语的。默默地把没燃尽的经文纸翻到上面,充分燃烧后,再把灰烬整理成一小堆。待明日清晨时分,父亲会早早起来打扫。
之后也询问过父亲,所谓鸣鞭烧纸是否确有成效?父亲便笑着说,不过是寄托生人的哀思罢了。我想之所以肃穆,便是心诚则灵的成分居多吧。
就如同《琅琊榜》中梅长苏与老先生交谈时所说的,所谓世事万物,无处不道。隐于山林为道,彰于庙堂亦为道。只要其心至纯,不作违心之论,不发妄悖之言,又何必执念于立身何处?
同理,唯守己心清明,何虑其有无?所寄哀思亦如是矣。
回到院中央完成最后一拜后,父亲才会领着我回房与姐姐们一起准备开饭。小姐姐每每好奇地问我都去了哪里,我总是缄口不言的。她便会凑过来悄声说,她知道院中央的大灯笼里住着的是姜太公。我笑了,她便也笑了。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父亲便回房,紧闭房门,不会再出来了。母亲也去佛堂诵经了。姐姐们便会争相拿出各自准备好的扑克牌,摆摆八门什么的卜问新一年的运势。
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总要笑闹一番的。
如今,这一张张昔日的笑颜,历经了世俗的诸多打磨。再见时,已非昨日那般少时摸样了。
到了这一代,除了两个与我相差无几的外甥女外,余下的只能从大人们的讲述与书本的记载中去领略关于年的习俗与文化了。

作者简介:
林静,中学教师,笔名自游木。红尘陌上游离木,巷院幽清守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