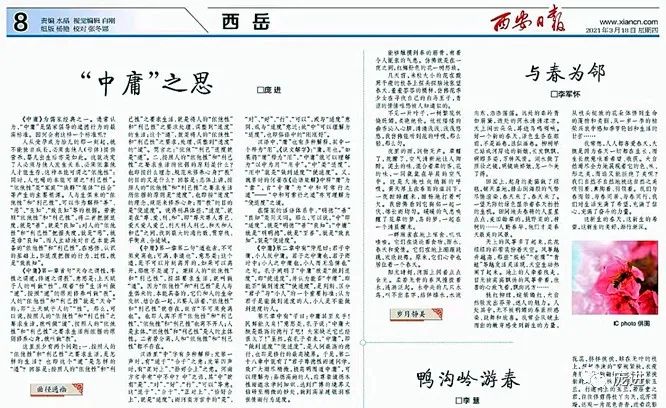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成为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经典之一。一般认为,“中庸”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如何会有这样一个标准呢?
人从受孕成为胎儿的那一刻起,就不能独自成长,必须由他人(母亲也是他人)提供营养。生下来后,若没有他人提供吃喝,婴儿的生命就会终结。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人才能生存的本能,可谓之“依他性”。同时,婴儿都是把吃的喝的,本能地吃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可谓之“利己性”。“依他性”,是“家庭”“族群”“集体”“社会”等产生的主要根源。
人的与生俱来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可以作为解释“善”“恶”“良知”“致良知”等的根据。兼顾“依他性”和“利己性”,将二者把握适度,就是“善”,就是“良知”;对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失度,就是“恶”,就是非“良知”,而人主动地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在感悟、认识的基础上,作适度把握的行为、过程,就是“致良知”。
《中庸》第一章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顺着“性”生活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
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就是“天命”的,即“上天赋予人的”“性”。那么,可以说,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就叫做“道”,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修养心身,就叫做“教”。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是怎样的生活?也即这个“道”是怎样的“道”?回答是: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处理、调整到“适度”的生活;这个“道”,就是将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处理、调整到“适度”的“道”。简言之:“依他”“利己”适度就是“道”。
第二,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也即按什么理念、规范来修养心身?“教”的目的又是什么?回答是:总体上讲,按照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之要求生活所依据的原则是“适度”,也即按“适度”的理念、规范来修养心身;而“教”的目的是“使适度”。说得稍具体些,“适度”,就是在“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中庸》第一章第二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意思是:“这个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
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按其要求生活,就叫做“道”。因为“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具备的,它们和人的生命交织、结合在一起,只要人活着,“依他性”和“利己性”就存在,故言“不可须臾离也”。也即人离不开“依他性”和“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也离不开人;人是主体,“依他性”和“利己性”是人的主体性。二者若分离,人和“依他性”和“利己性”都不存在。
汉语中,“中”有多种解释。发第一声zhōng时,有“适于”“合于”义;发第四声zhòng 时,有“正对上”“恰好合上”义。河南省的方言中有“中不中?中”之语,其“中”就有“是”“对”“好”“行”“可以”等意。这“适于”“合于”“正对上”“恰好合上”,就是“适度”;而河南省方言中的“是”“对”“好”“行”“可以”,或与“适度”意同,或与“适度”意近:故“中”可以理解为“适度”,也即俗语中的“刚刚好”。
汉语中,“庸”也有多种解释,其中一个释为“用”。《说文解字》:“庸,用也。”。如果将“庸”释为“用”,“中庸”就可以理解为“以中为用”“用中”。“中”是“适度”,“用中”就是“做到适度”“使适度”。又,魏晋时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释“庸”为“常”,言“中庸”为“中和可常行之道”——“中和可常行之道”亦可理解为“使适度”之道。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明德”“善”“良知”是同义词。那么,可以说,“中”即“适度”,就是“明德”“善”“良知”;“中庸”就是“明明德”,就是“至善”,就是“致良知”,就是“使适度”。
《中庸》第二章中有这样的话:“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是:“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反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时时都能做到适度;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做事没有顾虑和畏惧,越过了度。”
在这段话中,孔子阐明了“中庸”就是“做到适度”,即“使适度”,并认为能否“中庸”,即能否“做到适度”“使适度”,是判断、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君子是能做到适度的人,小人是不能做到适度的人。
《中庸》第三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人们缺乏它已经很久了!’”显然,在孔子看来,“中庸”,即“做到适度”“使适度”,是人间最高的德行,也即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于是,《中庸》第二十八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号召:“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可以理解为:“品德高尚的人,应尊崇道德本性而追求学问知识,达到广博的境界又钻研至精微的妙处,做到高屋建瓴洞察世情而行为适度。”
(2021年2月2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以《“中庸”之思》为题载于2021年3月18日《西安日报》第8版。)

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之誉。微信号: pang_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