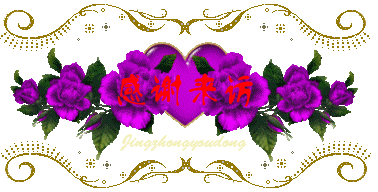龚德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


哭调
文/龚德明
人死不能复生,因为哭调,这可惜又添一重。
说可惜,是因为我们虽然活着可以看到哭调,但每个人都不可能看到属于自己的哭调。
“未知生焉知死”“为礼不敬,临丧不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等,皆在文化源头的上游留下了重生怀死——作为传统的行行足迹。
生命的仪式感,是对生命的尊重。即便是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一直激流汹涌、滔滔不绝,但对生命仪式感的重视,从来未被忘却。这似乎说明了作为丧礼的哭调,山高水长,一路弯弯曲曲、兜兜转转、淙淙流淌,不被湮灭的原因。
扬州民间由二胡、长号、云锣、檀板等合奏的哭调,依旧延续着其不绝的生命。尽管现代化、工业化、商业化,悄然淹没了属于传统的很多东西。甚至,我们对死也有了更为达观、理性的看法。
在网上搜“哭调”,一下子便跳出很多视频。黄土高原地区,有大鼓,有云锣,不见了二胡,却多了唢呐;西南地区,有芦笙,有排箫与小号,却未见其他。民间乐器的使用,大概也体现着文化区域性的差异。但同样的表现“哭调”,曲调却与扬州的民间演奏并无二致,皆低徊悠长、哀怨不绝。让人不禁想起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

死,是生的归途。面对死,生无所逃遁。或许,正是因为死的存在,生才获得了作为生的伟大意义。王小波有句话说得非常有趣,大意是,某人死了,其便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件事。但面对死,我们依旧会习惯性的伤悲。
对于死者,难过的理由有很多,却也有足以自慰的存在——这便是“哭调”。
随着年岁的增加,参加了很多死者的葬仪,也目睹了许多的“哭调”。突然发现,哭诉者的哭词(往往对应哭调),并不是对死者完全客观公正的评判,常常把死者生前的一切拔高了千丈万丈,说如何不辞辛劳照顾妻儿,说如何忠厚待人,说如何孝敬老人可为风范,等等。其实,死者生前也许是个赌徒、酒鬼,也许是个忤逆之辈,也许还有其他不良嗜好。此刻,全部一笔勾销。“死者为大”——最后一场,没必要留下其作为生的不光彩之种种于世。这对于生,确实算是个圆满的句号;对于聆听哭调者,又不啻是个教育:生当如是也。
时代向前,我觉得这哭调,应该也算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妥妥地保存着不使遗失了才好。但,我们从来只对流失远走的珍惜,对眼前存在的往往漠视。
情,死于无趣。生命也死于无趣。这是个趣大受追捧的时代,这当然是活的进步——是思想进步的表征,是通达看待世事的态度。
某日酒宴小聚,众人皆大快朵颐、酒酣耳热。一扬剧资深票友说愿献段“哭调”,说是《哭麻将》,情境编排是:一老头痴迷打麻将,有天老头自摸——杠后开花(麻将的一种“糊法”,手气特别顺的一种情境),老头子大喜,不料血压突升,脑溢血,暴毙而亡。老太婆哭:
老头子啊,我叫你不要打麻将啊——
你要打麻将诶,你打起个麻将来啊,你的两个眼睛啊笑得像个二筒(麻将里的牌——二饼)啊——
你现在呀两个眼睛闭起来了呀,你的两个眼睛嗯——像个二条(麻将里的牌)啊——
老头子啊,你的眼睛闭起来啦,你躺在白板(麻将里的牌)上了呀,你把我老奶奶(扬州方言,意为老婆)嗯——留下来在这里独钓(麻将的一种“糊法”)啦——
此一刻,空气里酒香味、菜肴味填满了空间,笑声涌动,把气味鼓动着推出餐厅的包间之外。
哭调,表达的不再是伤悲,而成了类似于“二人转”、“脱口秀”的存在。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