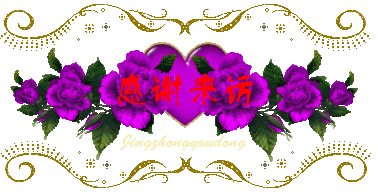超越物欲的情爱
——评剑言一白闪小说《思绪桂花香》
文/袁锁林
剑言一白的闪小说《思绪桂花香》,像一首精致唯美的散文诗,也像一篇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童话。
一个边防兵投稿三年,一个女编辑因文生情,思绪联翩,情不自禁不远万里前往孤岛,听边防兵解读他思绪中的实际是一块大礁石上的图案的桂花树,眼眸里闪动着泪花。
女编辑爱慕边防兵文采、品性,而不在乎对方是个普通的哨兵以及彼此相隔万里。这个超越现实的爱情故事,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难以置信。然而,笔者还是相信社会生活中确有这样圣洁的情爱的存在。只是这样的情爱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了,它像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已经凤毛麟角了。
诚然,社会是复杂的,世界是多彩的,人也是千差万别的,选择也是自由的。我们不可以也不可能要求恋爱中的男女都像女编辑与边防兵那种超越物俗的情爱,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超越物欲的情爱的存在以及崇高情爱的意义。一个为国成边为大家舍小家把对家乡的思念寄托于桂花树的战士不值得爱吗?一个注重精神世界看重心灵交流的女编辑不值得理解与尊敬吗?是的,生活在世俗的人们,不能不现实,但过于现实,失去对崇高的追求,就失去了精神的高地。
还值得一提的是,《思绪桂花树》的爱情故事浪漫,语言抒情富有诗意,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美轮美兵。
或许,这就是闪小说《思绪桂花树》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之所在。
2015年10月5日


吴跃建,笔名:剑言一白,当代中国军旅微型小说代表作家。系福建作协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会员,当代微篇小说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福建闪小说委员会会长。
1978年2月入伍,曾是从军26年的上校政委。1988年与微型小说结缘以来,先后创作发表900多篇军旅微型小说。作品独树一帜,以军旅为视角,内容涵盖了军人、军营、军属,战争、战斗、战场等,主题昂扬,军魂闪闪。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人民前线》《前锋文艺》《福建文学》《百花园》《写作》《小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当代闪小说》《短小说》《厦门文学》《厦门文艺》《闽西日报》《福州晚报》、泰国《中华日报》、新加坡《大士文艺》等报刊,小小说(闪小说)作品分别入选《金牌小说》《中国当代微小说精品集》《2016年中国闪小说佳作选》等;2006年7月,小小说《财富》获“新浪网”全国征文一等奖,闪小说《失忆的老兵》《满门忠烈》等先后获全国征文一等奖;2017年1月,《幸福街一号》获“牡丹疾控杯”中国首届微篇小说年度总冠军大赛铜奖;著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军人赠言集《军旅赠言》;中国第一本军旅闪小说集《军魂闪闪》。



永远的手机号
【编者按】
父母为了不再让儿子战友和同学老往电话卡里充钱,决定销号。为了纪念牺牲的英雄,移动公司决定担负英雄手机号的费用,使之成为永远的手机号。感人的文字,推荐精品欣赏!(永铭家珍)
夜深了,宾馆内一对心力交中的农民夫妻静静地坐着。
面对反复地翻看手机短信的妻子,质朴的丈夫轻声地征询说:“我们来8天了,这宾馆一晚要大几百,后天回吧?”
眼圈红肿的妻子回答道:“嗯,听你的。再说家里的地和鸡鸭……”
丈夫的声音有些嘶哑:“明天去趟移动公司吧?”
妻子眼中喻着泪水:“可是,我想经常拨打……”
丈夫递给妻子一个小本子,继续劝说道:“里面的短信、微信和联系人我全记下了,就留手机吧……不然,还会有人继续充值,心不安啊。”
翌日。移动公司内,营业员解释着:“根据规定,手机销号需要本人带身份证……”
夫妻俩志志不安地走进经理办公室,丈夫说:“麻烦您了。我儿子是消防员,来不了了,永远留在天津港……销号时能不能把他战友和老同学们充值的话费帮我们取出来,我们要捐给村里的孩子……”
室内,哭声一片。
走出去的经理回来了,递过一个小包,说:“收好了,除了手机里的话费,还有我们公司赞助的5万元。公司决定,此号码所产生的费用我们负责,永不销号。”
2015年8月13日
作家、网友点评节选
@杨学勇:短短的400字,竟然让人泪流满面!凝练的笔触,字字珠巩,一个手机号引出许多回味和思索。
@周琳熙:作者思想敏锐,由新闻写出时代感很强的闪小说。永远不销号,留下的是永远磨灭不了记忆、怀念、精神、榜样。
@刘松武:永远的军旅写作、永远的军人情怀,感动!


外婆的长征
外婆的家,在“山高路远坑深”的闽西。
外婆说,16岁结婚的那年冬天,大雪纷飞的一个晚上,家里来了几个远方的“亲戚”。
外公要跟“亲戚”走了,留下一顶斗笠作为念想……外婆凝视着外公下山的背影,背上那斗笠左右晃动,把她的心也晃空了,也晃颤出漫长的岁月……
第二年,外婆生下我的母亲,取名笠子。
出生于篾匠世家的外婆,回娘家三个月后,把所有的生命能量注入斗笠里,开始了砍、锯、切、剖、拉、插、编、织、削、磨的日子。
一年、二年、三年……渐渐地,外婆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女篾匠。
斗签,是外婆心中的图腾。漫漫长夜的孤寂、生活的苦涩和艰辛,让她那瘦削的身板始终挺直。亲友劝她改嫁,她一脸坚定:“不,我有男人,我等!”
外婆的平顶斗笠,打破了自古尖形斗竺一统天下的格局。
保安团来彻查斗竺的来历,外婆举着闪亮的篾刀说:“路上捡的……”
家乡解放了,县里来了解“红军斗笠”的故事。外婆开腔了,声情并茂:“那年家里来了扎着绑腿、背着长枪和平顶斗竺的人……”沉浸在回忆里的外婆,像新娘子一样可人。
纪念碑和书上没有外公的名字,外婆那斗笠的故事,就像漫山的蒲公英花,随风吹走。
每天,她总是坐在门口,凝视着村口的那条路,把篾丝剖得又细又长。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领导送来“烈士证书”,要她说说红军的事。
86岁的外婆老了,身躯像那被大雪压弯的竹子,手颤悠悠地握着“红军斗笠”,愣了好久,沉陷的眼眶,突然泪水
涟涟,然后号陶大哭。
2013年10月14日
作家、网友点评节选
@郝勇:没有豪言壮语的外婆,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始终坚守和坚信,大爱无言!
@乐智强:文章写一个红军军嫂70年默默坚守的故事,以斗签为主线,反映另一种牺牲精神。她坚守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一种长征精神。
@聂新阶:我们难忘“身躯像那被大雪压弯的竹子”的外婆形象。人形象典型,长征精神永远屹立不老。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