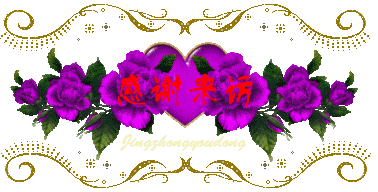柯月霞, 中学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集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生活 创造》《福建教育》《厦门教育》《集美风》,厦门日报晚报等。爱旅游,爱阅读,爱写字,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煤油灯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山村,印象中那时候的夜晚来得特别快,仿佛太阳一下山,整个村庄就陷入一片黑暗中。暗夜里,每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总是很暗,那时我家虽然装了电灯,但只是15瓦的,光线不太亮,而且为了省钱,总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开电灯。
我家厨房没装电灯,妈妈总是赶在天黑前做好饭,催我们快快吃。夏天的夜晚,我们会把饭端到小院里的石桌上,一家人在淡淡月光下,星光下,边吃晚餐边聊天。冬天的夜里,我们在厨房用餐,妈妈把煤油灯高高地放在窗台上,大家在微弱的油灯下吃饭。
我记得那盏煤油灯是玻璃制成的,有一个铜做的灯头,一条棉绳灯芯通过灯头伸出来,灯头四周有许多个爪子,旁边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或下降的小齿轮。棉绳的下方伸到灯座内,灯座内注满煤油,棉绳便把煤油吸到绳头上,只要用火柴点着绳头,并罩上灯筒,煤油灯便亮了。
我们家的厨房有三个土灶,一个做饭,一个炒菜,中间一个最大的灶煮猪吃的食物。灶前塞满了柴草,厨房的门边有一张小桌子,平常收起来靠在墙边,吃饭时才张开,墙边还有几张小板凳,我每次吃饭都是坐在一块圆圆的石凳上。煤油灯光线昏暗,那时又常常吃稀饭配小鱼煮芥菜,鱼小刺多,灯光又暗,我记得有次我不小心卡了一根鱼刺在喉咙,咳了很久还出不来,下不去,把血都咳出来好多了,最终才吞下去了。
煤油灯总是根据需要在厨房里的角落里移来移去,炒菜时煤油灯就移到灶前去,父亲把一个大杯子倒放在灶前,然后把煤油灯放在杯子上,以便让灯光照的范围更大一些。有时不小心,煤油灯便被摔倒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心血来潮要为我们炸油条,一切都准备好了,油也热了,面条也下到油锅里了,整个厨房都是浓浓的香味,都是喘喘喘油翻滚的声音。眼看着油条就要出锅了,父亲夹起一条,刚要放到盘里去,“啪”的一声,煤油灯摔倒了,哪个地方不好倒,偏偏整个地倒进油锅里去了,天啊,那天炸出的油条,全都有了浓浓的煤油味,但我们都舍不得扔掉,仍然吃下去,父亲说,反正都是油,应该没事的。还真是没事呢,反正那晚肚子没痛。
关于煤油灯的记忆,挥也挥不去。



杆秤
杆秤可算是“国粹”了,它制作轻巧、经典,只由秤杆、秤碗、秤盘或秤钩三个部分组成,携带方便,使用也极为便利,至今依然能在市面上见到。小生意人带上一杆杆秤,或别在腰间或放于笼萎之间,买卖一来,随手一握秤杆,挂好秤花,栓好秤盘,边秤边笑容满面地说:“你看,秤高高的。”于是买家便觉得得到了很大优惠,欢喜地付钱,这样的买卖,比起电子称更有人情味。记得小时候,我家也有一杆杆秤,秤杆由木头做成,深色,长约40厘米,一端粗一些,一端细一些,靠近粗的一端有一个秤钩,秤钩附近有个小孔,一根粗的线栓在孔上,这就叫做提纽,秤杆上等距离地刻着许多星花,秤物时,提起提纽,将秤碗挂在秤杆上,移动所挂的位置,直到杆秤处于平衡,然后根据星花看斤两。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就学会了用杆秤。每天早上我都用备宾挑着菜到菜市场卖。刚开始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不熟练,我每次拿起杆秤手都有点发抖,还常常把平它掉到地上,甚至砸到脚,一副手忙脚乱的狼狈模样。但乡亲们却还是很喜欢买我家的菜,有的会打趣地说:“小姑娘,你到底会不会秤啊?”然后看着我呵呵笑,有的甚至拿过秤杆自己秤了。卖完菜我便匆匆往学校赶去。我那时当班干部,管着班级的钥匙,我得赶去开教室的门。记得有几次,我去晚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被挡在门外,那时,挑着谷宾的我真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啊。那些卖菜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赚钱的不易,我于是更刻苦地学习。
但那杆秤最终却让我不小心弄断了。我记得我当时很怕被父亲责骂,于是把秤接好,放在厨房里的灶头上,然后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最后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刚要开口,奶奶先出声了,奶奶说是猫跳上跳下摔坏了杆秤的,父亲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那件事就那样过去了,却那么深地刻印在了我的心坎里。
如今,我到菜市场,见到的大都是电子称,不管买多少东西,服务员往电子秤上一放,价钱就呈现出来了,比杆秤便利多了,杆秤便也越来越少见了,但那些杆秤买卖的岁月却刻印在了我们这代人的心里。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