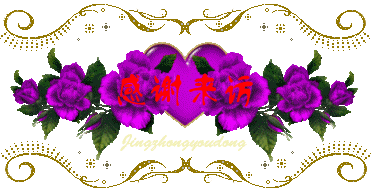柯月霞, 中学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集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生活 创造》《福建教育》《厦门教育》《集美风》,厦门日报晚报等。爱旅游,爱阅读,爱写字,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犁 耙
犁耙我住农村,和植物走得很近。田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除了犁田和。我家走廊的墙角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农具,半蹲的木犁,倒竖的齿耙,蜗居的竹萎,悬挂的弯嫌,还有锄头、谷宾等等,像个小型农具展览馆。每天吃罢早餐,父亲、母亲便拿起农具到地里干活,我的双休日、寒暑假也成了农人,和父母亲一起到田地里去干活。
我会割稻,会锄地,甚至会踩打谷机,但犁田和却是父亲的专利,因为犁和很重,犁田很难,在扶犁的同时还要一手牵着牛绳指挥牛拉着犁按规定的路线走,这种活几乎都是男人做的,女人只能打打下手。我常常给父亲打下手,所以对这种高难度的农活也不陌生。
犁田耙田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并没有任何教科书可以学,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农民口授身传,父传子,子传孙,并在实践中学习掌握的。犁田是有讲究的,对于不同的田地犁法不一样,比如,犁种水稻的田,可以一条接一条犁,犁种红薯、花生、青菜的地,就要先考虑犁几条作为一哇,才决定从哪里下犁。犁田还要讲究深浅,犁插得太深,牛拉不动,不小心还会把犁头拉断,而且会把生泥带起来。犁插得太浅,不能完全把地翻松,土太少,不利于作物生长。犁田还要犁得均匀,不能留下“犁骨”,特别是水稻田,犁骨太多会给插秧带来麻烦。
所以农人要把犁扶正,扶稳,并和拉犁的牛配合好才能把田地犁好。
犁好田地后,就必须把田地耙匀耙平。水稻田如果耙不平,一头高一头低,就有可能让一边的水稻晒死,一边的水稻淹死。农人耙地时要注意观察,要把高处的泥土往低处耙,耙水稻田不能放太多的水,水太满就看不出高低了。有经验的农人很快就能看出该从哪里耙起,并和牛配合默契,省时省力,没经验的农人可能就会劳累一整天,喊得唇焦舌燥,依然没把地耙好。
父亲耙水稻田时,我常常跟在身边,把花生叶用脚踩进泥土里,让它在泥土里腐烂成为肥料。有的水稻田有虹蚓,犁耙一上,蜓蚓全都从土里跑了出来,农人们便一条一条捡起,拿回家去喂鸭子。我却很怕虹蚓,有次蜓蚓特别多,长长的,肥肥的,黑黑的,一条一条水在稻田里翻滚着,出其不意地就碰到我的脚腿肚,我吓得几乎流下眼泪,却不敢说,闭着眼,咬着牙,硬是把田里的花生叶踩完,如今想起还觉得脚底凉嗖嗖的。
曾经的经历,成了如今取之不尽的宝藏,每当情绪陷入低潮,想起那些艰苦的干农活的经历,便觉得信心重又回到了心中,而更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簸 箕
有些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逝了,可关于它们的记忆却会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里,比如簸箕。
我小时候住在老屋,老屋的客厅很大,墙壁上挂着菜篮、簸箕,还有蓑衣和斗笠等物品。我对那个大大圆圆的簸箕印象最深,因为它盛满了我童年里的许多欢乐,许多笑声。
簸箕是用竹片做成的,因为使用时间长,那些竹片已被打磨得极其光滑,颜色也不似竹子那般的米白,而是变成深咖啡,而且似乎还闪着一层光泽,乌金乌金的,平滑,冰凉。在炎热的夏季,我常常把簸箕放到地板上当椅子坐,冰凉冰凉的,很是舒服。记得那些蝉鸣声声的夏日午后,我们坐在簸箕里听收音机里的说唐故事,常常,门前池塘里男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妇女们洗衣时闲聊的声音,也随着阳光探进门里来,于是便觉得那些时光无比热闹,又无比安静,很美。
庄稼收成的时候,簸箕便开始忙碌了。花生,黄豆,麦子,龙眼等等,一拨一拨地往家里搬回来,奶奶便把它们倒在簸箕里,均匀地散开,一个个放到屋顶上或者小院里晒。天气一变,就把簸箕连同谷物搬进屋里来,这样晒东西干净又方便。记得那些夏日的午后,四周静悄悄的,屋顶上簸箕里的谷物也静悄悄地在阳光里躺着。奶奶坐在走廊上,戴着老花镜补衣裤,奶奶的身旁躺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一头,绑着长长的花布条,当鸟雀扑棱棱飞下来啄食时,奶奶便拿起竹竿,往屋顶上一扬,那些叽叽喳喳的鸟雀们便又扑棱棱飞走了。如今想来,那幅画面,真是美丽温馨极了。
在我们闽南农村,农人们常常用簸箕来簸去稻米或者花生中的杂质和空壳。记得当花生晒干后,奶奶便开始用簸箕簸花生,双手各抓着簸箕的一边,向上一下一下地扬起,把比较不饱满的花生和杂质往簸箕的末端簸去,然后熟练地把杂质簸出去,接着就开始捡花生,颗粒饱满的装一袋,拿去卖钱,颗粒不饱满的留作自己吃,或者拿去榨油。我们小孩往往要参加捡花生,所以印象特别深。
我最喜欢的,还是萝卜干收成的时候。奶奶把萝卜干切成条状,放在簸箕里,晒到半干,傍晚时分,把簸箕搬到客厅,放在地板上,往萝卜干上撒上盐巴,我和妹妹便洗净脚Y,兴高采烈地踩簸箕里的萝卜干,使劲踩,使劲跳,边跳还边唱着歌,那些萝卜干在我们的脚下,渐渐变得温润,奶奶把它们一一塞进瓮里,封上口,不多久就成了下饭的美味了。
簸箕不忙的时候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一人拿一个簸瓮,坐在里玩扑克,丢沙包,叠着糖果纸玩,做着童年里喜欢做的那些事。
策箕的光阴里,有亲切的奶奶,有我可爱的童年,以及童年里那些欢乐、那些歌声。簸箕里的光阴,成了我心底里最美的记忆。


犁、耙、小簸箕、甲笠(音译)
(名词解释)

犁
犁 犁是一种耕地的农具,是由在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其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或机动车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
犁主要有铧式犁、圆盘犁、旋转犁等类型。在5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农民就开始尝试使用犁。早期的犁是用Y形的木段制作的,下面的枝段雕刻成一个尖头,上面的两个分枝则做成两个把手。将犁系上绳子由一头牛拉动,尖头就在泥土里扒出一道狭小的浅沟,农民可以用把手来驾驶犁。到公元前3000年,犁进行了改进,把尖头制成一个能更有力地辟开泥土的“犁铧”,增加了一个能把泥土推向旁边的倾斜的底板。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最初可能仍名“耒耜”。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早期的犁,形制简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开始用牛拉犁耕田。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只有犁头和扶手。而缺少耕牛的地区,则普遍使用“踏犁”。踏犁也称“镵”、“脚犁”。使用时以足踏之,达到翻土的效果。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
踏犁形如匙,长六尺许。末施横木一尺余,此两手所捉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县所踏处也。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犁之深于土。
至隋唐时代,犁的构造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曲辕犁。除犁头扶手外,还多了犁壁、犁箭、犁评等。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共有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可以控制与调节犁耕的深度。长达2.3丈,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唐代犁的复制模型。其原理为今天的机引铧式犁采用。唐朝的曲辕犁与西汉的直辕犁相比,增加了犁评,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改进了犁壁,唐朝犁壁呈圆形,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前进的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杂草的生长。

在古代欧洲使用的犁从青铜时代起,基本上就没有怎样改变过。只有犁嘴从公元前十世纪起一般用铁代替了木头。这时的犁在耕田时由犁田人提到一定的高度,需要相当大的气力。犁出来的沟垄既不怎么直,也不怎么深,因此要犁过两遍。在犁第二遍时要和第一遍的方向形成直角。
德国农民采用传统的犁耕地在欧洲,公元前一世纪就已经使用一种新式的犁。它有个轮子控制犁地的深度,这就使犁地的人省力。新式犁有犁刀划土和一个模板翻土,犁出来的沟又深又整齐,而取代了以前的犁田法。新式犁比旧式犁要重,拖起来需要相当大的力气,因此农民用牛来犁地。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则开始用马耕田。现在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包括中国),仍然使用犁来进行耕作。类似犁的器具也称为“犁”。
犁分为翻转犁、旋耕犁、五铧犁、解放犁、犁壁。

北方:耙

南方:耙
耙 耙(bà)是农业生产中传统的翻地农具,曾经是农家必备的农具之一。也是中国武术器械之一,由农具演化而来。铁齿钉耙,耙齿锋利似钉,攻击性强,也兼有兵器的作用。因耙可击,可耙,一度成为军中最利的武器之一。耙的击法有“推牵”、“扁身杀”、“倒头打”、“大斜压”等;防法有“对打对揭”、“直起磕”、“扁身中拦”等。武术单练套路有“九齿钉耙”和“荷叶耙”;对练有“耙进枪”和“耙战刀牌”等。读bà。于表层土壤平整的农具;较大。耕作深度一般不超过15厘米。耙在中国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称之为“铁齿楱”。元《王祯农书》记载有方耙、人字耙等。

南方:耙
耙,在中国南方,特别是闽南地区,特指用铁制作的,有长齿,用牛拉动,用以平整田地的工具,形状如图。
簸箕

小簸箕才是作者笔下的簸箕,是圆的,直径一米左右。

大的,闽南话叫:甲笠(音译)
大簸箕又称斗枪(音译),闽南话叫:甲笠(音译)。直径近二米,是农村晒谷子等物品的东西,好放好收。圆状,周边凸起,用竹篾编制而成,将斗枪平放在地或者放在几个木凳上,可以在里面晒谷物、豆子等,是农村晒谷子等物品的东西,好放好收。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