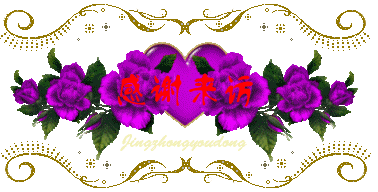柯月霞,中学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集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生活 创造》《福建教育》《厦门教育》《集美风》,厦门日报晚报等。爱旅游,爱阅读,爱写字,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红龟印
福建·柯月霞文

闲逛中山路,在局口街,我看见一个大大的红色标志性雕塑,外来游客争相与它合影,以证明自己来过厦门。这雕塑名叫“龟之戏”,是做红龟棵的模具,我们称之为龟印。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吃红龟棵,尤其喜欢花生陷的,咬一口就觉得满嘴甜香,非常美味。现在每次上街买菜,我都会买一两个,回到家,泡一壶茶,品着茶,吃着龟棵,任往事历历浮现眼前。记得小时候,过年过节的仪式很是隆重,每个摆上供桌、餐桌的东西,都是家人亲手做的。那时没有什么零食,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解解像。三月吃米糕,五月吃棕子,六月吃汤圆,八月桂花糕,十二月吃甜棵,正月初九天公日,就吃我喜欢的红龟棵了。那时我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做龟棵的模具,做红龟棵时,有时几家一起做,有时全家集体行动,很是热闹。过节前一两天,家里人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材料其实简单,米,糖,花生或者芝麻,再去屋后摘几片芭蕉叶,或者黄懂叶,就可以了。
做法却有些麻烦。米要先浸上一天一夜,然后要去石磨里磨成浆。这项工作往往是我配合奶奶完成的。磨米看起来简单,却很讲究技术。磨的时候,用力要均匀,每次放进石磨的米也要等量,太多太少,或者推磨太急,磨出来的米就粗细不均,做的红龟棵也就不好吃了。
米磨成浆后,要把水分滤去。奶奶会用竺筐装满满一筐草灰,把米浆倒进一块大大的棉布里,紧紧绑好,然后放进草灰里,这样让水分慢慢滤干,米浆成了米块。奶奶就把米块册成条状,让我们小孩揉搓,再分成大小均等的一小块,就可以开始包陷了。

红龟棵的馅一般是花生或者黑芝麻,也有用绿豆的,都要先炒熟,碾成粉。记得那时,奶奶总是把炒熟的花生放在簸箕里,去皮后,拿一个空酒瓶,来回不停地压,直到把圆圆的一粒粒花生,压成点点粉末,满屋子飘荡着浓郁的花生香味。如果是黑芝麻,那就更是香得没谱了,只是奶奶很少用芝麻做馅,大概是因为芝麻比较贵的原因吧。花生粉中要加入糖,这样馅料才又甜又香。
我曾经帮奶奶压过花生,听着那“搭喊喊”瓶子碰碎花生米的声音觉得很是美妙,我常常边压,边抓一把放进口中,直到把一张小嘴弄得满是花生粉。
印模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了。等到奶奶把花生陷放进米块里包好,等到她在印模里抹了一层花生油后,我就开始帮奶奶印模了。我学着奶奶的样子,把包了陷的米块,放在印模上,轻轻地按压,然后在它上面,放上一张芭蕉叶,然后左手按着印模,右手按着米块,轻轻翻转过来,把印模拿开,一个漂亮红龟棵就做成了,最后把它放进蒸笼里,一个个整齐地排好,蒸好,就可以好好享用了。
这些年来,街上卖起了红龟棵,甚至连更好吃的黑草龟也卖妈妈渐渐地也不再自己做龟棵了,过年过节时就从街上买。家里这个传了两代人的红龟印,渐渐地成为了多余之物,成了我们细怀往事的凭借了。





老水缸
福建·柯月霞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家家户户都会有几口缸,那些缸都是用粗土烧制而成,体型都很大,缸壁成坡形,底部到缸口逐步张开。乡民们根据它们的大小,给它们派用途,有的用来装稻谷、米,有的用来装黄豆、花生,还有的用来装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家的那口老水缸。
那时每户人家厨房的角落里,都会摆着一口大水缸,用来储存一家人的用水。水缸的上面会盖着一个缸盖,以保持缸里水的干净。水缸里的水一般够一个家庭用上一两天,等水用完了,把水缸清洗好,再装上新的水备用。
我家的那口老水缸,比别人家的水缸小巧得多。我家隔壁的那户人家,孩子有七八个,一家人吃吃喝喝、洗洗刷刷用水量大,他们家的水缸就特别大。记得小时候的我站在他们家的水缸前,总要站起脚尖,才能看得见水缸里的水。而我们家小院里有一口井,这口井里的水据说水质不够好,不能吃喝,只能用来洗刷,我们家吃喝的水要到五、六百米外的一口古井里去挑回来,所以我们家的那口水缸只用来装吃喝的水,所以比较小巧。洗渊的水用另一个更小的缸装。
我很小就学会了用吊桶从井里提水。那时力气小,无法一口气把一桶水从井里提上来。奶奶就教我,每次只打半桶水就好,提不动的时候就把绳子靠在井沿一下,喘口气再接着提。我就这样半桶半桶地提,也终于能帮妈妈把洗刷的水准备好。
那口古井离家颇远,而且古井很深,提水比较困难且有危险,所以妈妈一直没让我们去。可妈妈很忙,每天忙完地里的活,一回到家还要忙家务。有时回到家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要做饭做菜了,才发现水缸里没水了,还得跑去挑水,便会急得手忙脚乱。我看在眼里心下一动,想帮妈妈的忙,去那口古井里挑水回家。
怕妈妈不答应,我决定先斩后奏。那天放学后,我便鼓动妹妹一起去挑水。于是我们俩用一根扁担,一前一后抬着一个铁桶,拿着一个吊桶,便雄赵赵气昂昂往古井走去。

黄昏的古井旁很是热闹,有挑水的,有洗菜的,还有洗衣服的、从古井里提水冲凉的,乡亲们一边忙一边聊天,个个看起来都很开心。我却尚喘不安,那个井壁上长着青苔的古井,实在深不见底,我简直不敢往下看。
我慢慢把吊桶往下放,感觉碰到水了,就胡乱一甩,然后就往上提,提多少算多少。有时不小心甩重了,装了满满一桶水,我便只好把绳子靠着井沿,慢慢往上拉。乡亲们见我提水那么辛苦常常会主动帮我。
每次我和妹妹只能抬半桶水回家,半路上还得歇一两次脚。
我们最最喜欢在那条长长窄窄的巷子里歇脚,那里风最多,还有一大片阴凉,扯开喉咙喊一声,还能听到回音,因而常常歇在那里玩一下。
我和妹妹抬两三趟才能把水缸装满。看我们干得不错,妈妈便默许这份工作。还教会我装水前先把水缸洗干净。水缸不洗不仅有一层污垢,还会长青苔。我站起脚尖,手拿晒干的丝瓜嚷死劲搓,把水缸洗得干干净净,才把辛苦抬回家的水装进水缸里。
那口水缸,从童年起一直伴着我们长大,一直到我和妹妹出嫁了,它还默默地守候在厨房外的那个角落里,一直到家里装了自来水,它也还在默默地工作着,妈妈早已习惯了用它装水,妈妈把水缸放在水龙头下面,拧开水龙头存半缸水,要用水就用飘从水缸里罔。
算起来,这口老水缸在我家已经有四十几年了,它成了妈妈至爱的宝贝。莫兰蒂来临前,妈妈怕水缸被砸坏,特地抬到屋里去。有妈妈这般的爱护,这水缸如今看起来还挺新的,一点也不显老。望着这口老水缸,和妹妹一前一后抬水的情景,便历历在目。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