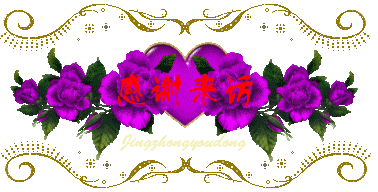柯月霞, 中学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集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生活 创造》《福建教育》《厦门教育》《集美风》,厦门日报晚报等。爱旅游,爱阅读,爱写字,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茶盘和公鸡碗
福建·柯月霞 文
有些物品,带着岁月的痕迹,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心便盈满了柔情。比如我家抽屉里收藏的那个茶盘和公鸡碗。
茶盘是铁的,白色,边沿是粉色的,但在岁月的打磨中,已锈迹斑斑。正中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建设祖国的图画,一支红梅从左下角旁逸斜出,衬得那图画更鲜艳美丽。翻过盘子来,只见底部正中清晰地印着小小的几个字“1970.12-4”,这个茶盘至少有五十年的历史了。
从我懂事起就有这个茶盘的记忆了,因为除了简单的几个碗盆外,它几乎是我们家唯一的像样点的器具了。别看小小的这个盘,在那时我们家它的作用可大了:有客人来时,父亲会拿它当茶盘,把一个小茶壶和几个小茶杯往它身上一放,就可以在小院里开始泡茶了。大人们坐在矮凳上,泡着茶,聊着天,我们在旁边的空地上跳橡皮筋玩游戏,等到茶水慢慢快把茶盘注满了,父亲便会把茶壶和茶杯拿出来,端起茶盘,随手把盘里的茶水往墙角的地上泼去,要是父亲拿出茶壶和茶杯时刚巧被我看见,我便会一边跑过去一边喊:“我来泼,我来。”父亲便会把茶盘放到我手上,叮嘱我走路小心别摔了,而我双手端着茶盘走到墙角泼水时,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因为我知道背后有父亲和客人赞赏的目光。
过年过节时,这个茶盘便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餐具。父亲把油炸好的炸枣、菜丸、鱼块,一个个叠放在盘子里,堆成像一座小山似的,放进一个大竹篮里,挂到房间屋顶正中的那个铁钩上,以防老鼠偷吃。等到客人来时,父亲才把篮子取下来,拿了东西招待客人。那些日子我总是喜欢站在房间里,抬头望着头顶上的那个竹篮子,闻着篮子里铁盘上那些炸枣菜丸肉块散发出来的浓浓的香味,心里无数次祈祷客人快快到来。
公鸡碗是我小时候常用的,碗口敞开,比现在用的碗要大好多,碗边画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或者鱼,配一朵鲜红的花,几片绿叶。那时生活条件困难,一年难得见到几次餐桌上有鱼有肉,所以就把把鱼和鸡画在碗上,这样就仿佛就有鱼有鸡了。公鸡碗很粗糙,有的甚至凹凸不平,不过它很耐用,不易打破,记得好几次我洗碗不小心摔了,也没摔破。那时我最怕把碗摔破了,至少得招来妈妈的一顿骂。
关于公鸡碗,还有一个很深的记忆。记得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从来没做过夜宵的妈妈突然心血来潮为我们做甜稀饭,我和妹妹特别兴奋,守在锅灶边,一直等到那锅热气腾腾的甜稀饭熟了,妈妈撒下几把白糖,搅拌好,晋到公鸡碗里,装了满满两大碗,妈妈让我和妹妹共吃一碗,另外一碗她和父亲吃。一向听话的妹妹那晚不知怎么就是不听妈妈的话,一定要独自霸占两大碗。妈妈连哄带骗最后让步让她独自一人吃一碗她也不让,一定要两碗全包。弄得妈妈哭笑不得最后只得宣布两碗都归妹妹所有。妹妹终于破涕为笑,拿起汤匙就开吃,可是那小小的三岁孩子能吃多少啊,只见她还没吃几口,汤匙一放,歪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如今,从碗橱抽屉里翻出这个茶盘和公鸡碗,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竟然觉得一切的人和事好像真的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院子里的那口井
1982年父亲烘培龙眼干赚了点钱,又东拼西凑凑了五百元,于是在村口申请了一块地,开始打地基盖房子。房子盖好已经是第二年初夏了。积蓄没了,还欠了不少钱。父亲于是决定自己装修。他买来工具,自己当师傅,妈妈和我当小工,开始粉刷墙壁。虽然至今我家的墙壁还是有点凹凸不平,但总算是牢固的,三十年来都没有渗漏的现象发生。父亲不会铺砖,就请姑丈来帮忙,几个月过去,一套房子就装修成功了。整整五间,还有一个小院,那年夏天,我们搬到新居住,我心里对父亲佩服得不得了。
住进新房,父亲又开始动手建厨房,还砌了围墙,围墙上的栏杆也是我们用印模版一个一个做出来的。之后父亲发现还少了一口井,于是念念叨叨想挖一口井,但因为挖井是件技术活,也担心挖下去会不会有泉水,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动工。
1984年国庆,表弟来找我玩,听到父亲说想挖一口井,便满口赞成,还说愿意帮忙挖井。父亲一听立马站了起来,拿过锄头就想开始挖。母亲连声喊着等一下,然后跑进房间抽屉拿出一枚硬币,往小院里一扔,硬币一直往前滚去,最终居然停在厨房附近的那个角落。母亲说就从这里挖,这里准有泉水。父亲拿来一个策箕,依着簸宾画了一个圆圈,表弟拿起锄头就开始挖井了。就这样,父亲和表弟轮番挖着,我和母亲轮番用谷箕把土提到门外的路边去,井越挖越深,土越来越湿,母亲拿来水桶装土,再往上提,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路过的三舅妈看见我们在挖井,也来帮忙了。第一天只挖了一米多,第二天一起床,父亲便又开始了工作。第三天,第四天,父亲越挖越有信心。渐渐地,土越来越湿,渐渐地,有水渗出来,到第五天黄昏,听父亲说,水漫到脚躁了,这时已经整整挖了6米了,父亲说,就6米吧,六六大顺。于是我们家的井就算挖好了。
隔天清晨,我一起床就往井边跑去,探下头往里望,啊,水已经有很多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拿来水桶,提了一桶又一桶,相互泼着玩水,开心极了,自豪极了。
父亲又自己砌了井沿,还用瓷砖割出了数字,贴上去,把几个重要的数字——1984年10月永远地记录下来。
刚开始,我们只敢用这井水来洗刷,后来父亲还抓来几条鱼放进井里,慢慢观察着,发现连日来小鱼儿都在井里游来游去,便宣布这井水可以吃。于是我们便开始放心地用这水来烧水煮饭洗衣洗澡。后来,周围渐渐地有新房子建成,有新的井出现,我家这口井的水就渐渐不够用了,水位慢慢地低下去,到后来提上来的水就不太清澈,刚好村里开始装自来水管,我们便吃自来水,这井水只用来洗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地忽视了这口井的存在。前天回娘家,看见井沿上放了一块大大的瓷砖。父亲说那是妹夫搬来放上去的。于是这井成了饭桌茶桌了,每当黄昏,住在附近的妹夫便会来到这里,坐在井边陪老丈人聊聊天泡泡茶。我问父亲,井里还有水吗?父亲说没啦!早在几年前就没了。
虽然这井里的水早没了,可是这井依然存在,还有那些关于这口井的记忆都会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上,它是父亲勤劳与智慧的见证,也是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的见证。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