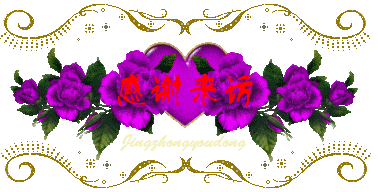薛薇莎,集美第二小学语文教研组长,集美区专家型教师,热爱阅读,致力于引领学生阅读的研究。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在水一方、三叶草,文章散见于《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峡两岸》《厦门文艺》等,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个人散文集《人闲桂花落》,厦门女作家散文合集《遇见》。



老家的龙眼树
薛薇莎
夏日黄昏,回家。看到市场边上有许多卖水果的小摊,摆满了黄澄澄的龙眼,一颗颗饱满诱人,我不禁满口生津了。想起了老家的那些龙眼树。
在闽南的农村,龙眼树是常被作为庭院的绿化树栽种在房前屋后的。龙眼树也像乡村里的孩子一样,好种易活,生命力极强。或者一颗种子,或者一株枝条,落到土壤里,一到春天,细雨绵绵,便抽枝发芽,曾赠地向上长,不过两三年的功夫便可长得和平房一样高了。自家种的龙眼树和果园里的不太一样,一般都不加修剪,任由它自然生长。如果长得不够高就开花了,人们常常会把花成串地折断,让它先长高长大了再挂果。所以乡间的许多龙眼树都长得很高大,树冠巨大如伞,有的树长在土地肥沃阳光充足的地方,竟也像树一般亭亭如盖,炎热的夏日能遮蔽起几百平方米的树荫,丰收的季节可以采摘上千斤的果实呢!以前爷爷就有这么一棵巨大的龙眼树。每到夏天龙眼成熟的时候,我就盼望着采收龙眼的商人来收购。因为树很大,不借助工具是采摘不到的。当大人们爬上树采摘的时候,我就在树下静静地等待,不时会有丁丁冬冬的果粒掉下来,有时还砸到我的头上,砸得脑袋生疼。掉下来的果粒往往熟透了,黄灿灿的颜色真惹人喜爱,剥开皮露出圆滚滚的果粒,雪白的果肉包裹着黑亮的果核,塞进嘴里那甜丝丝的味道,真美啊!爷爷种的龙眼树真不少,果树的品种也不尽相同,有早熟的,晚熟的,水分多个头大,味道甜但个头小的。老人依照他对三个儿子的疼爱程度进行了分配。当然那棵长得像榨树的分给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我的小叔,我的父亲是爷爷的长子,分到的只是几株长势不太好的龙眼树。原来龙眼树还藏着爱的秘密。后来,我的父亲自己盖了新房,又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每到夏末秋初的时节,果子成熟了,他便会打电话召唤我们回去尝鲜了。
回家后,父亲总会牵着小孙子来到树下,让小孙子拿着篮子在树下等着,自己爬上树去摘果子。龙眼树很老了,那在树上身手已不再敏捷的父亲也老了,六十几岁的人了。孩子归来的时候满心欢喜地采摘果子,看着他爬上高高的树干,用他那青筋突起的手吃力地把成串的龙眼折断时,我的心里真的有很多的感激和不安。龙眼年年挂果,年年甜,而父亲却一年年老去了。摘完龙眼我们坐下来品尝,真甜啊,新鲜的带着特殊的香味,一颗一颗不知不觉消灭掉不少,那种甜味直沁人的心田。
前几天妈妈打来电话,说今年家里的龙眼丰收了,我也该回去尝尝鲜果了,我也该去看看那一年比一年老的父母了……



母亲的蒸笼
秋天,阳光洒满了农家小院。在这样灿烂的日子,母亲总喜欢把家里衣被什么的拿到阳光下晾晒,还搬出了一个很大的蒸笼。这个大蒸笼是圆形的,竹子编成的,有一个大大的锥形的盖子。多年的熏蒸,使得竹片有些发黑了,黑亮黑亮的,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痕迹,在秋日的阳光照耀下越发闪亮。
乡下的年节,总会制作各种糕点,在土地里摸爬滚打的农民们,对食物总是保持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以美食犒自己的辛苦劳作,以这样的方式庆祝着一个个节日,岁月就这样平静地流逝着。
二月二,龙抬头”蒸芋头糕;清明时节蒸“鼠壳粿”,端午,包粽子;八月中秋,蒸红龟粿。要是临近过年,那蒸笼上就日夜不停地忙碌着:蒸甜的、咸的各色年糕……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有很多的时间都在厨房忙碌着。闽南人称厨房为“灶脚”,多么形象的称呼,农家妇女们不就是围着炉灶,围着锅台忙碌的平凡的生活吗?蒸笼就这样伴随着如水的日子,静静地流淌。
春天,黄的红的小花开满乡间的时候,有一种小草也在这时候探出了脑袋。毛耳耳的,嫩黄嫩黄的,很可爱。在这时节,村子里的妇女们,总会相约着,去采摘这春季里最可爱的小草,它叫“鼠壳草”,这是制作“鼠壳棵”的最重要的原料。乡村的妇女们,呼朋引伴,拿着口袋,带上干粮,去赴一场春天的约会。采摘完“鼠壳草”,在阳光下晾晒几天,然后蒸熟,再用石白一下一下地把它们捣碎,成为墨绿色的团儿。揉进磨好压干的糯米团,再包进花生和糖拌成的馅料。一个个圆圆的,黑乎乎的,用“红龟”模子,印出漂亮的花纹,放在抹上油的香蕉叶上,样子很可爱。但是只有在蒸笼上经过蒸汽的洗礼后,才能呈现出它独特的滋味来。母亲总是忙碌的,每一个环节她都亲自操劳着,为的是能蒸出她心目中最好的味道。把准备好的鼠壳棵放到蒸笼里,在锅里加水,然后,用木柴在灶膛里生火,氨盒的蒸汽很快蒙绕着整个灶间,母亲的额头、脖子上都沁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她总是挂一条毛巾在脖子上,不时地擦拭着。当蒸熟的鼠壳棵鲜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馁虫一个个被勾出来了。母亲总把第一个出锅的美食送到我的嘴边,看着我不时地吹着热气,着急负梦的样子,她总是眯着眼睛笑。在她的心里,美食就是馈赠给家人最好的礼物。乡下人,不善于表达爱,捧出美味,看着你津津有味地享受,露出满意的微笑的时候,她们的内心装满了那么多的满足和幸福。
初夏,空气中飘来温润的味道,端午临近了,妈妈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浸泡棕叶、香菇,准备糯米、海沥干、虾仁、鹤熟蛋、三层肉,还有芋头,前期工作繁琐而复杂。先把糯米用清水浸泡,一个个圆头圆脑的芋头削皮,磨成芋泥。再把家里那口直径达到一米的大铁锅烧热,放入油开始把棕米和海奶干混合炒香。棕米是炒过后,所以更加香、软、糯。炒到两三层熟的时候放入磨好的芋泥,这时候棕米的粘性很大,需要不停地翻动才不会粘锅,爸爸妈妈常常轮番上场,很辛苦。
炒好的棕米装了两大盆,三层肉和鹤帛蛋、香菇等配料一盆盆放好,再拿来晾干的粽叶,开始包粽子了。这种时候通常还要邀请几个邻居大妈帮忙,他们用咸草做绳子,把棕叶折成三角形,先放入糯米,再塞入三层肉香菇还有鹤帛蛋,最后再加一点糯米,把棕叶压紧,扎上绳子,一个粽子好了,绿莹莹的格外好看。大半天过去了,粽子基本包好了。爸爸开始生火,把那大铁锅放入水烧开,再把硕大无比的竹制蒸笼放上去,然后把粽子一层一层码好,盖上盖,开始蒸粽子啦!
渐渐地,飘出棕子的清香了,真的很诱人。几个小时过后,等爸爸把最后一把柴火熄灭,就可以开锅啦。哇,太壮观了!一个个棕子经过几个小时的桑拿浴,一个个出落得水灵灵的,漂亮极了。
过年了,母亲又围着蒸笼忙碌了,甜糕、芋头糕、红龟……故乡的灶台很温暖,因为有母亲在。母亲的一生,流连于灶台和蒸笼之间。灶台边,忙碌一天三餐。蒸笼里,蒸出年节的好味道。这乌黑的蒸笼,蒸出的美味,让我深深地怀念,那是家的味道。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化传媒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