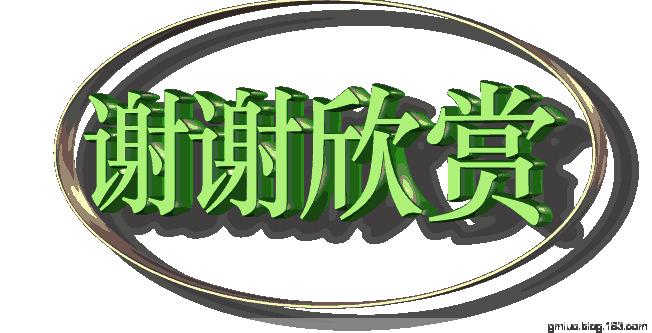薛薇莎,集美第二小学语文教研组长,集美区专家型教师,热爱阅读,致力于引领学生阅读的研究。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在水一方、三叶草,文章散见于《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峡两岸》《厦门文艺》等,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个人散文集《人闲桂花落》,厦门女作家散文合集《遇见》。



飘香端午节
“艾叶青青门前挂,棕香飘飘五月里。龙舟竞渡池水上,又是一年端午节。”农历的五月初五是端午节,闽南人习惯称之为“五月节”。此时正是初夏草木深深的时节,总是飘散着沁人心脾的香味。
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是集美盛大的活动,在凤凰花绚烂的龙舟池畔,每到端午节前夕,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龙舟队伍,他们泛舟水上,鼓声阵阵,吃喝声声,“一二一,咚咚咚,一二一”齐心划浆的气势,总在龙舟池上飘荡。龙舟在水上,观众们在岸上,震天的呐喊助威声响彻耳畔。传统竞技活动“抓鸭子”最有趣,竞技场就设在水面上,参加者要走过一根涂满滑油的圆木柱,然后打开一只盛鸭子的木箱,再跳进水里去抓掉下去的鸭子。场面火爆,颇具闽南风情。漫步在集美学村的石板路上,初夏的风轻轻地吹,裹着花的香味悠悠飘来,是茉莉还是玉兰抑或是柜子花,都是记忆中初夏的味道。
每到端午节,妈妈总会去采摘艾草和树枝挂在门上辟邪祈福。树树,在闽南随处可见,寻找长得碧绿鲜亮的树枝,剪成一段一段的带回来。艾草就种在房前屋后,折一段,和榨树枝扎成一把插于门帽,悬于堂中。艾草,也叫艾蔼,是一味芬芳化浊的中药,有较强的驱毒除瘟作用,也可以煮水洗澡,用来驱蚊。据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记载:“五月五日,端午悬蒲、艾、榨枝于门,粘符制采胜及棕相馈遗。竞渡于海滨……或十余日乃止。”这就是端午,家家飘散着淡淡的艾草的香味。
端午节最开心的事还是能够尝到妈妈包的粽子了,每年都盼着这五月的盛宴。肉粽是用料最丰富也是最好吃的粽子,清水洗过的长长的筹叶折成三角形,放入海沥干炒制的糯米,包入鹤剪蛋,三层肉、板栗、虾仁或干贝,压紧,再放入糯米扎成牛角形。放在竹制的蒸笼上蒸,筹叶特有的淡淡的清香浸润到糯米和配料中,叶子的香裹着食物的香,怎不叫人垂诞欲滴?爸爸总把蒸好的棕子用长长的竹竿挂着,一个个绿绿的粽子悬在空中,很是诱人,满屋都飘着棕子的香味,让人心醉的味道。
艾草青青,棕香浓浓,最是一年端午香,热闹忙碌的端午风俗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年又一年地沿袭下来。汪曾祺先生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是的,正是由于这些传统的民俗,使得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切入点用来做情感的慰藉或者宣泄。



青箬笠绿蓑衣
和友人在一家茶馆喝茶,茶馆精巧别致,掩映在一片绿竹之中。落座,烧水,冲茶,抬头看见茶室的墙上挂着一件蓑衣,落满了时光的灰尘。一屋子的茶香飘飘袅袅,让我恍惚之间好像回到了熟悉的闽南乡村,看到了记忆深处的烟雨三月,农民们披着蓑衣耕田插秧的情景。衰衣,曾是我们生活中的平常之物,但岁月的更替,时光的流转,它渐渐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留在了时光的深处。
在乡村,蓑衣是平常之物,用蓑草编制而成,制成上衣与下裙两块,厚厚的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不透水也不透风。穿裴衣一般戴斗竺,是落雨时节很好的防雨防风的用具。据说古时候,蓑衣还是猎猎时很好的“护身服”。
斗笠蓑衣,烟雨三月,耕田插秧,构成了颇具古意的乡村画卷。春寒时节,农民们已经开始了一年的忙碌,翻土耕田,撒种插秧,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不想错过了耕种的好时节。春天雨水多,蒙蒙细雨飘飘洒洒,穿着衰衣的农民在田间忙碌,雨丝悄悄落下来,沾在蓑衣上,又轻轻滑落下来。蓑草一根一根,密密地缝制,结实紧致,很好地抵挡住了雨水的侵蚀,斗篷式的设计,也方便农民们活动双手。农民们穿着蓑衣,或者赶着牛吃喝着犁地,或者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或者挑着萝筐把刚采下来的新鲜蔬菜带回家。蓑衣,是乡村的符号,是抹不去的乡愁。
我也曾穿过蓑衣,在下雨的清晨去放牛。蓑衣原本是给大人穿的,可是禁不住对它的喜爱,我闹着要穿它。母亲拗不过我,给我穿上厚厚的蓑衣,然后把衣领两侧的带子拉紧,免得雨水渗透进来。蓑衣散发着一股特别的草的气息,质朴可爱。穿上它,再戴上斗笠,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稻草人,从远古的时代走来。小小的瘦弱的女孩子,牵着一头老黄牛,走过一条一条的田埋。春天的草嫩嫩的,绿得晃眼,牛吃得很认真,贪婪地把绿草卷入口中,来不及咀嚼便匆匆咽下去。天与地之间,好安静,只听见沙沙的落雨声和寒寒宰容的牛吃草的声音。时光仿佛静止了,定格成一幅画,画面中有一头老黄牛和一个戴斗笠穿蓑衣的放牛娃。
塑料雨衣的出现,冷落了老式的蓑衣,它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悬挂在仓房的墙上,和静立的锄头,笨重的犁,长长的爬子在一起,成了一种记忆。人们很少再使用它,把它遗忘在时光的长河里,它的身上落满了灰尘,孤寂地躲在黑暗的角落,属于它的时代已经结束。后来,它也曾出现在农家的博物馆里,或者某种刻意制造出来的仿古的设计里。就像在今天这个茶馆里,有意营造出来的返琐归真的氛围。我们总是猝不及防地迎接着许多新的事物,又在不经意间把曾经熟悉的朝夕相处的事和物遗忘。新旧更迭,时光流转,我们也只是这长长的时光之流的过客。你的来,你的去,波澜不惊,终将被遗忘。
没有被遗忘的是藏在古诗里的蓑衣,诗人手中的笔让这些家常之物,有了某种诗意和美好。孩子们能够在诗词中遇见远古的画面,让过去和现代连接。
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里这样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條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夫戴青箬笠,穿绿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每一次教学生学这首词的时候,我总喜欢和他们一起想象画面,想象一下着在春天里,桃花红遍,一位戴青箬笠,穿绿蓑衣的渔夫超脱的形象。诗歌历久弥新,让我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觅得一方宁静之地,觅得那一份从容闲适。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廖廖数笔,牧童的快乐和饱饭后的放松惬意就跃然纸上了,这便是吕岩笔下的《牧童》。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听着悠扬的笛声,卸下疲惫的牧童,来不及脱下蓑衣就躺在月夜下享受悠悠的晚风。劳动带来的疲乏之感,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愉悦,留下的只有快乐。
唐代诗人柳宗元在《江雪》一诗中也有关于蓑衣的描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周的山连绵起伏,空旷极了,只有在那宽广平静的江上,一个披着蓑装戴着笠的老渔翁,孤零零地坐在船上独自垂钓。山水之间的景物,孤独的穿着衰衣的老翁,写满了诗人的清高与孤傲。琐事缠身,压力巨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吟诵这首诗,向往着做一个身穿蓑衣,孤独垂钓的渔翁,把所有的烦心事抛在脑后。
蓑衣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今日再次遇见它,让人仿佛回到了古朴的乡野大自然中,闻到泥土、草木清香。隐藏在诗词里,不曾褪色,传唱千年,仍然美好如初。






中华作家原创文学协会·中华文创文学社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