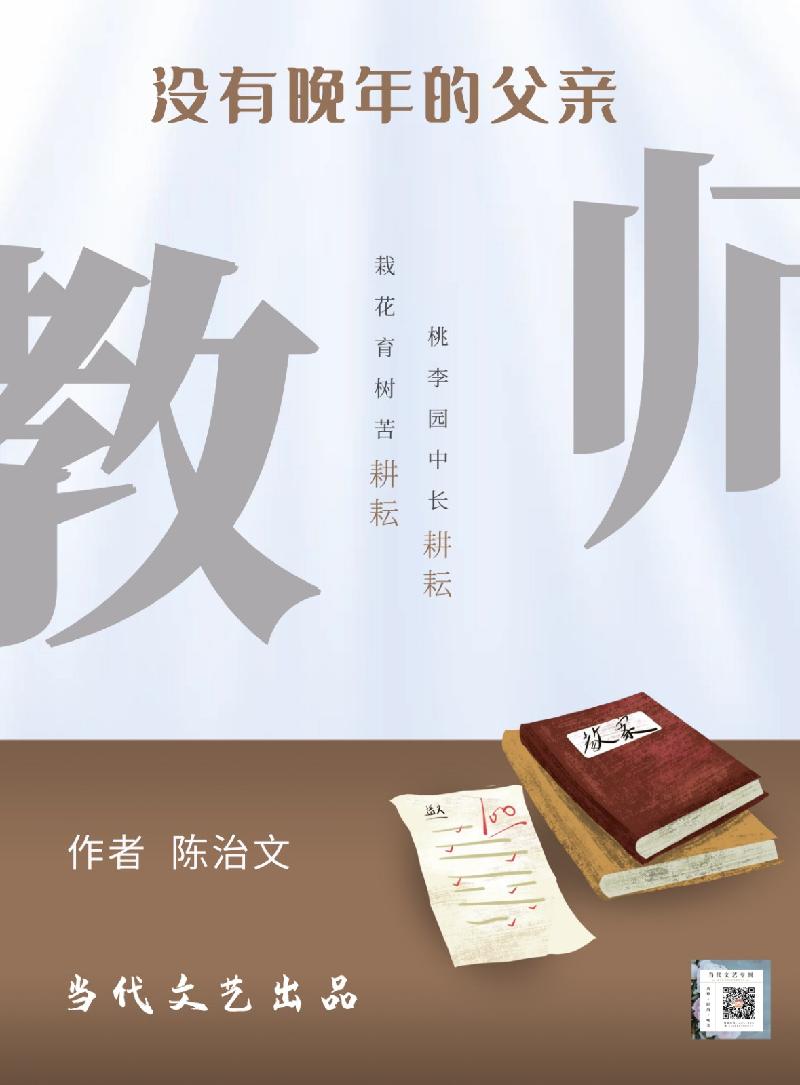
没 有 晚 年 的 父 亲
文/陈治文
献给今年一百岁的我亲爱的父亲,他沒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
——题记
如果父亲还健在的话,今年应该100岁了。然而他却在49岁那年就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我的父亲,他沒有晚年。
父亲的童年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上有五个姐姐,只有他这么一个独子。老来得子,又是个老巴子,可谓掌上明珠,实在是惯得不得了。家里再困难,生活再清苦,他还是吃好的,穿新的,甚至还上了好几年的私塾(五个姑姑沒有进过一天书房门)。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一直读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个小文化人了,这点墨水也成了他后来谋生的本钱。
然而世道艰辛,难以预料。我的祖父祖母在父亲还不满十六岁的时候就先后去世了,五个姑姑也都己先后出门嫁人了。剩下父亲孤苦伶仃一个人,只好独自谋生自食其力了。于是他就靠上私塾识的几个字办起了私塾馆,当起了小小的私塾先生,去教一些七八岁的小娃娃们。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些小娃娃们个个顽皮跳骨,很难管教。不知父亲玩了什么招数,居然和一帮孩子们处得很好。书又教得不错,小娃娃们个个都很喜欢他,学的也认真。家长们见自家小孩子在书房里听先生话又吃字,加上父亲一手好毛笔字,大家也就相信他,甚至很尊敬他,纷纷送自家孩子来父亲私塾馆念书。就这样,他从少年一直设舘教到而立之年。这当中虽然由于战乱有过几次中断,但还是继续教了下来。这一教就教了十几年,成了方圆好几里有名的陈先生。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先是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接着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靠教私熟那点微薄收入胡口,活得很艰辛,直到二十八岁才好不容易成了家。婚后第二年生下了我(后来又先后为我添了个弟弟陈淦文和妹妹陈湘文)。那个时候由于农村识点字的人很稀少,因而他先后教过的学生后来大多数都成有用之材了。有的参了军,成了军官;有的入了党,当了地方干部;有的做了医生。还有更多的人后来也成了人民教师。
父亲私塾一直教到解放初期的1952年。那时候人民政府重视乡村教育,开始大力创办公办小学。由于师资奇缺,就广泛进行招考教师。己经30多岁的父亲也就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他顺利地通过了政府组织的招收公办教师的考试,成功地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当时由县文教局统一分配,安排他到离老家周巷近30里的临泽镇最东面,紧靠兴化的一个水乡小村小李庄,去创办了高邮县小李初级小学。尽管那个时候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但父亲没有畏缩,硬是坚持了下来。一个人先后教起了一至四年级的大复式。全校也就是父亲一个人,既当校长,又兼教工,既要上课教学,又要烧火剥葱,名副其实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离家远,交通只有靠两条腿。加上是水乡,还要过河过港等摆渡,交通很不方便。所以父亲很难得回家一趟。偶尔到临泽镇上开会了才顺便溜回去一次,第二天吃早中饭就又往学校赶了。这来回六十多里还是很累人的。

离家远回家少也就让父亲一门心思扎在工作上,以校为家,以生为友。他教过十几年私塾,又不断自学,后来还参加中师函授並且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文凭,成了不但有正式编制而且还有合格资质的人民教师。小李庄是偏僻水乡,交通极不方便,出门全靠小船。人们生活贫苦得很,但尊师重教气氛却特别浓。加上父亲一手好字,和干部群众关糸非常的好。父亲在小李庄一带人气旺,威信高,就连现在七八十岁以上的人,还记得当年那个很了不起的陈先生。父亲教学成绩也比较拔尖,年年评为先进教师受到县文教局的表彰,没几年就被提拔调任完小校长了。先后在临泽地区的菱湖小学,东沟小学,韩庄小学工作。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曾到当时最艰难困苦的荡区甘垛一带教过学。这当中,父亲受尽了磨难。由于闹饥荒,人们肚子吃不饱,都饿得皮包骨头,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想上学呢!父亲尽管也得了黄肿病,(一种因长期饥饿营养不良而得的病)仍坚持带领老师们天天是早上上门请学生,中午上门带学生,放晚学还要分头送回家,并且一再的约学生第二天要来上学。就连这样,还是有流生,有的学生甚至外流,和大人去安庆了。但由于父亲的努力,他们学校流失的学生是最少的。就凭这一点,还受到了当时县里开校长会时的口头表扬。

1963年,父亲被调至周巷靠近家的新颜河小学工作。虽然离家仅二三里路,但他一心放在学校里,一门心思扑在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上。有这么两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他喜欢家访,时常放学后要到学生家中走一走。和家长交流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因而他结交了一批又一批的家长朋友。父亲家访从不告状,都是肯定学生在校的良好表现和学习进步的情况,学生们也就都喜欢他到他们家去。二是他爱校如家,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晚上和寒暑假都要去护校,从不要临泽界首路远的客籍教师护校。护校是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他完全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风雨无阻从不无故间断过。在新颜河小学五年多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安全方面的事故。同事们都很敬佩他,尊重他,每个学期都受到上级表彰,还曾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彰。三是父亲的一手好字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一进腊月门还沒有放寒假,他就忙起来了,方园好几里的人慕名而来请他写春联。大家都知道他忙,所以早早把对联纸拿过来排队。父亲来者不拒,起早带晚写,白天照常去学校上班。过了二十四夜放寒假了,则天天在家赶写春联。经常是写得手发僵眼发花头发晕,抽支烟活动一下继续写。他说,一年到头难得一次,不能误大事。不少人家心,里不过意,总要带些鱼,鸡蛋,粘糕,馒头之类的东西来以表心意,但父亲从来不收,至多吃人家敬上的一支烟而已。
父亲遗憾地于一九六八年暑假期间英年早逝了。他没有晚年,但是他还是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活得还是很精彩的。父亲,你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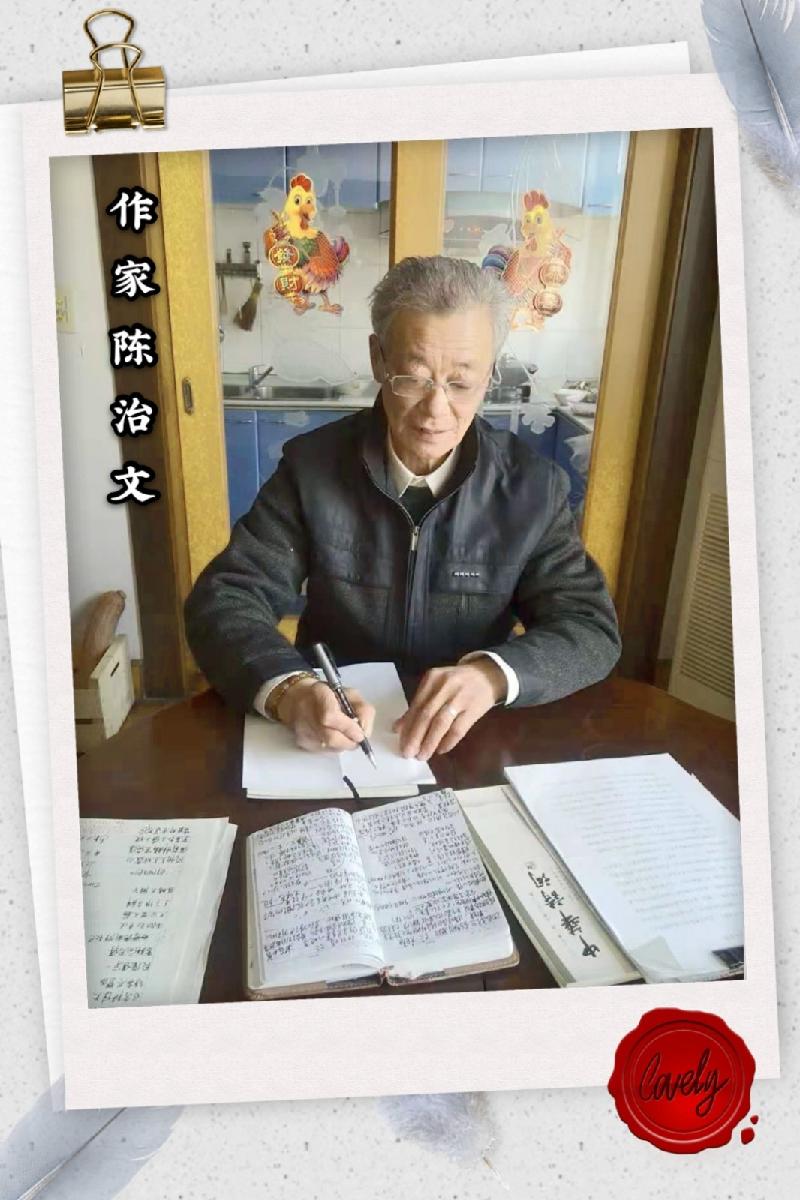
陈治文,江苏高邮人,退休教师。市作协会员。时有小说,散文,诗词等作品在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上发表。
【点评精选】
读罢陈老师《沒有晚年的父亲》一文,我被作者的情真意切所感染,我的眼前浮现了一大批五、六十年代扎根山区,坚守一方净土,无怨无愧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民教师形象。在这支队伍中,我仿佛也看到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与陈老师父亲所处背景不同,是正规的师范学梭毕业生,毕业后双双投入农村教育第一线。瞻仰那一代教育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岗敬业,他们为学生的辛勤付出,是我们这一代人无以比较的。岁月悠悠而去,但老一辈教师的敬业忘我精神,他们的大爱,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将永远的活在人民心中!他们的师魂永远伴随青山长青! 作品情感真挚,语言朴素,文章感人!推荐共赏。(点评:吕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