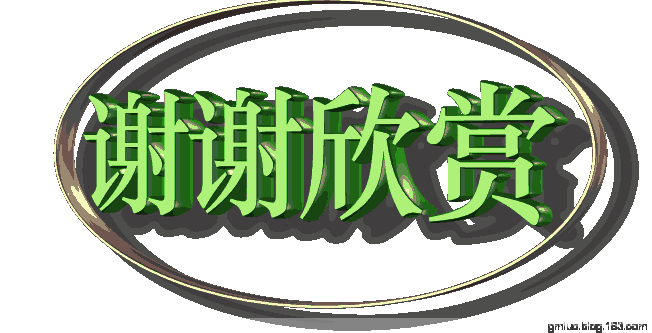薛薇莎,集美第二小学语文教研组长,集美区专家型教师,热爱阅读,致力于引领学生阅读的研究。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在水一方、三叶草,文章散见于《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峡两岸》《厦门文艺》等,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个人散文集《人闲桂花落》,厦门女作家散文合集《遇见》。



乡下的虫子
福建·薛薇莎文

乡村,像一幅古老的画卷,安静纯朴,依偎在山脚下,时光仿佛忘记了它的存在。日出日落,春生夏长,树木花草枯荣生息,牛羊牲畜也是一若又一茬地繁衍。还有那些不起眼的虫子也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多少的春秋。
虫子是无处不在的,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和我们做着邻居。它们的领地很广阔,天上,树上,水里,墙上,庄稼地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和整个村庄,整片山野共繁衍同生息,它们比村庄还要古老。
壁虎的长相不怎么讨喜,样子丑丑的,尖尖的小小的脑袋,夏天的夜晚,亮灯了,壁虎们开始活动了。它们守候在日光灯下,明亮的灯光吸引来了很多的飞虫蚊子,虫子们在灯光下快乐地玩着,嬉戏着,殊不知,它们是壁虎眼中的美味。吃完晚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壁虎怎么捕食。它们很安静,爬到灯下来一点声响也没有,巴在墙上一动不动。人们都说壁虎的脚上有吸盘,后来我在科普读物上看到,壁虎的脚上有壁虎的每只脚底部长着数百万根极细的刚毛,从而产生分子引力。你要是不了解它,会以为它就就像一个贴在墙上的玩具一样。壁虎捕捉蚊子的时候,先锁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慢慢移动轻轻爬行,快接近目标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舌头吐出,然后用舌头将蚊子粘住,吞进嘴里。吃完一只蚊子,壁虎又静静地巴在墙上,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每个夏天的夜晚,壁虎都是这样忙碌着。有时,它们吃饱了,就从灯下爬走了,速度很快,一眨眼间,就从这面墙爬到那面墙上去了。乡下的人们不讨厌壁虎,虽然它长得不太好看,但毕竟能抓蚊虫,又不打扰人们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和平相处。乡下人们管壁虎叫做“仙虫”,有尊称的意思。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在大扫除,用长长的高梁扫把打扫房顶和墙面,突然有一只壁虎窜出来,吓了我一跳,夏秋壁虎活动频繁,可是冬天似乎都躲起来了,我的扫把扫到一只壁虎,让我有些意外,最令人害怕的是,这只壁虎的尾巴竟然掉了,小小的一段,大概一两厘米长,在地板上不停地跳动,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听说,被壁虎的尾巴如果掉了,会跳到人的耳朵里,让人耳朵失聪,我赶紧插住了耳朵,跑了出去,动物学上说,壁虎在受到惊吓或者当你去捕捉它的时候,只要一碰到它,它的尾巴就会立即折断,壁虎也就乘机逃跑了,这种现象,在动物学上叫做“自割”,看来表我在墙上扫动的扫把让它受到了惊吓,其实它掉下来还不停摆动的尾巴,更让我感到恐惧。或许动物都有自卫的方法,想要在大自然中存活下来,都要有自我防卫的本事。
如果说壁虎对于乡下人来说还只是适合远观的虫子,那尿壳郎对于从小就在地里摸爬滚打的孩子们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的天然玩具了。乡下的牛走在路上,田块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地地绿色的粪堆。勤快的老人会用簸箕把牛粪扫回家晒干,可以做肥料或者种蘑菇。可是总有漏网之“粪”,有时,我们发现那些颜色已经发黑了,时间很长了的牛粪,就会很兴奋,因为有可能找到屎壳郎。
屎壳郎通常躲在粪堆里,一般由男孩子来找,他们不怕脏,个个都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的,整天不是上树去掏鸟窝就是在地上玩弹珠,所以这种脏活一般由他们来做。找来一根树枝,掏开已经被遗忘很久了的粪堆,终于发现了会动的黑色的虫子,那就是屎壳郎。

屎壳郎虽然生长的环境有点遭人嫌弃,但是它的样子并不丑。全身黑色,略带一种金属般的光泽,雄虫头部前方呈扇面状,表面有微微的皱褶。它有三对足,都像和子一样是它强有力的挖掘工具。男孩子们兴奋地把尿壳郎拿在手上把玩,女孩子们则表面上嫌弃它很脏,其实内心还蠢毒欲动,也想拿来玩玩。牛是食草动物,牛粪不算很臭,所以大人们也不怎么阻挠孩子捉尿壳郎玩。有时还会看到屎壳郎推着粪球前行,那个样子很可爱,它们很勤快,也被称为大自然的清道夫。据说澳大利亚的牧场因为牛羊的粪便太多,清理不过来,人们便引进了许多品种的尿壳郎,它们能够很快地清除牧场的粪便,让牧草快速生长。看来,这些丑陋的黑色的家伙也是有用处的。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屎壳郎还有推车客、黑牛儿、夜游将军等好听的名字。李时珍解释说,因为它们“深目高鼻,状如美胡,背负黑甲,状如武士,故有蜕邮、将军之称”。乡下的孩子并不懂得那么多,他们只知道屎壳郎是个调皮的家伙,是他们喜欢的可以当玩伴的虫子。
其实乡下还有很多长得挺美的虫子,例如蜻蜓啦,蝴蝶啦还有龙眼鸡,喜欢它们的通常是女孩子。男孩子有时为了讨好女孩子也会去捉这些好看的虫子。我最喜欢的是龙眼鸡。龙眼鸡经常停落在龙眼树上,是一种极其美丽的虫子。头上方红色的长鼻状的微微翘起,眼珠黑亮有神。绿色的翅膀上有清晰的脉络,分布着鲜亮的柠檬黄的花纹,艳丽夺目。它经常飞来,停在龙眼树的枝干上,用它长长的鼻子吸食龙眼树的汁液。闽南农村房前屋后都栽种着龙眼树,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漂亮的龙眼鸡,有时是一只,有时是正在交尾的两只,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快,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它。拿来家里缝衣服的线,用线绑住它的长长的鼻翼,让它不会飞走。或者拿来一个透明的罩子,农家盖饭菜的罩子就很合适,透气又能控制住它。通常玩累了,我们就会放它走。后来,我们知道龙眼鸡还有个学名,叫“长鼻蜡蝉”,但是这个名阐挂字很扬口,大家觉得不好念,还是“龙眼鸡”叫得更顺口。龙眼花鸡据说是害虫,但也从没发现这小小的虫子对枝叶茂密的龙眼树请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对它的喜爱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夏天也是知了欢唱的时节。渐渐听到知了的叫声了。起初还羞羞答答,隐隐约约的,盛夏一到,天气骤热,知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了,喧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夏天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
在乡下,夏天是忙碌而疲倦的。收割稻子,拔花生,种地瓜……农民们不仅要抢着收还要抢着种。大人们常常是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等到八九点钟,日上三竿后,天就热了,这时候就收工回家。正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大人们趁这个时候打时、小想一会儿。而小孩子是没有午睡习惯的。约上两三个伙伴,偷偷从家里溜出来,捉知了去了。找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竹竿顶端用刀分个叉,粘一些蜘蛛网,到树下寻找知了的踪迹。哪里的知了叫得欢就到哪里去。并不是所有的知了都会叫,雄的知了就很“稳重内敛”,只有雌知了耻噪地“滋滋”叫着。后来才知道那是知了在求偶,据说知了的幼虫在地下埋了17年,见天日变成成虫的时光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还不得趁着几个月的时间大声高歌。
枪打出头鸟,那只最吵的知了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目标。长长的竹竿被我们高高地擎着,对准目标,又快又准。啊,粘住了,一只知了成为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放在手上,看它明镜似的腹部,还有拼命挣扎的脚。有顽皮的男生会拿知了去烤,说味道很香,但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吃,我不能接受这样怪异的食物进入口中。我常常把知了请回家,让它在家里单独为我歌唱,它用嘶哑的嗓子孜孜不倦地歌唱着夏日的美好。

天牛是夏天里常见的昆虫,在高大的苦林树上常常可以寻觅到它们的影子。它们的样子很威武,黑色的盗甲,外搭白色的花衣,长长的黑色的触角动不动就直立起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和别人打一架。在苦谏树下,我们找到了一只天牛,它很凶猛,但其实动作并不敏捷,当你靠近它时,它并不急着逃走,而是耀武扬威地举起触角准备和你决斗,忘记了逃跑才是最重要的。哈哈,过度自负就是自寻死路。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天牛,放在手上,看着它困兽似的发脾气。有时还觉得不过瘾,再抓一只,让它们自己PK,我们则悠闲地观战,让燥热的夏天也多了一份乐趣。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夏天的夜晚是凉爽而惬意的,燥热渐渐褪去,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后便可以搬张凳子到院子里乘凉。萤火虫不知什么时候打着灯笼一闪一闪地出来了。小孩子们又有了玩耍的玩具了。看着故萤火虫忽闪闪地飞来飞去,兴奋地追逐着它们的影子。它们其实飞得并不快,不过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老实,它们更乐意和小孩子们捉迷藏。有时飞到小溪旁,有时躲到草丛里,有时明明看见它们落在一株植物上了,怎么一下子又不见了。不管它们飞到哪里,都给宁静的夏夜装点上了点点的荧光。找一个空的透明的花瓶子,放进两三只闪闪发光的萤火虫,静静地欣赏那个漂亮的瓶子,那是沉闷的夏日生活中最美的万花筒了。夜晚过去,白天来临,再看看美丽的“万花筒”,萤火虫已经奋奋一息,没有了昨日的光彩,想起昨夜的迷人和浪漫,恍然如梦。
乡下的虫子,是这片土地上的一种灵动的,富有生机的存在。它们把原本单调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生活里,能看着那么些鲜活的生命,以它们喜爱的方式与我们共存,看着它们飞来飞去,听着它们低吟高唱也是令人恒意和快乐的事。
乡间的风景,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铭记在我的记忆中。



《乡下的虫子》选自薛薇莎老师散文集《人闲桂花落》,感谢薛老师的支持!!!










主编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