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母亲的墓碑
我是一名无神论者,从不相信大千世间的神神鬼鬼,也不相信轮回和风水之说,更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什么照应。只相信相由心生、情自心发。
母亲因为走得太过突然,子女没有丝毫准备,既无备好的寿衣,也没瞄中合适的墓地。故乡是回不去了的,祖父母埋葬的地方,因为我们杨家恢复高考以后,连着出了几个大学生,有祖坟山开坼之说,在当地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祖父母埋葬的河堤,从过去孤零零的一个墓地,迅速发展澎湃成为一个"八宝山“公墓群。再想在祖父母坟地旁扦针,已无可能。至于菜地,倒是有,但在我们南方,菜地多为平坦低洼的地方,地下水源丰富,多不干燥,做墓地并不合适,已早被我在心内否决无数次了。
晴天霹雳,子女都乱了方寸,哥哥嫂嫂远在异国他乡,姐姐是居家女子,只有我一个男人拿主见。母亲的寿衣好解决,母亲过去在农村,帮老去的左右乡邻做惯了寿衣寿服,对这个黑不溜秋镶白边的捞什子见着就怕,经常胆战心惊的。我说:"就用全新的普通的棉制品替代吧",农村来的长辈有一点点异议,父亲、叔叔、姑姑们都赞成我的观点,旁人自再无话说。
母亲在世时,参加过我姐夫父亲的葬礼,站在碧云峰山脚下的山棱上,瞰看东方,阳光洗地,云蒸霞蔚,一片祥和繁荣景象,很是羡慕,母亲当时身体尚好,做为儿子的我并没在意,当时只跟母亲开了一句玩笑:"百年之后,我也给您找一块面向东南方向的好地方“。
葬礼照常办理,利用间隙到九鹤山殡仪馆周边去看了看,西边有墓地,且价格比较便宜,但西北方向相对冷清,不符合母亲在世时喜欢热闹的习惯,东南方向最下面一级台阶还有一梯平地,暂未开发,跑到墓地管理办去咨询,答曰:"半年后开发,价格是西北方向的几倍",心里有了谱,跟哥哥在电话里沟通,与姐姐、姐夫交流,决定母亲葬礼后骨灰暂寄存殡仪馆内,待东南方向墓地建成后再择日下葬。
一年之后,墓地建成,选了一个星期六,邀请部分亲朋戚友,大约三十人的队伍,将母亲的骨灰盒取出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热热闹闹将母亲下葬,诸事顺利。一周后墓碑刻成,安碑时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碑用水泥夯了三次,仍然向北倾斜,又夯了一次,还是右角稍微北偏,我站在墓地上看了看,家之南、墓之北,偏向角度是朝着家的方向的,立马指令夯碑的师傅们:"师傅们辛苦了,很好了,谢谢你们!"心里的小九九和震惊是不能与外人道的。
秘密在心里埋藏了很多年,实在忍不住了,跟妻子说了一下,都不能理解大自然中的一些神奇现象。
十年以后,父亲归山,与母亲合葬,墓盖是我这个儿子亲手打开的,母亲的骨灰盒用大红的丝绸包裹着,放在左手边,墓穴的底是纯黄土,前后历时十一年,红色的丝绸璨然若新,不曾腐损半点,心里的震惊更甚,骨灰盒底与黄土接触的地方也无丝毫毁损,这就更加玄乎了。
我不动神色的将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右边,用很快的速度盖好墓盖,看着师傅们用胶水粘合好,默默地想着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些难以置信的事。
一同参加合葬仪式的,还有农村来的亲戚朋友,消息还是不径而走,说什么我的母亲葬了风水宝地,消息传到我耳朵边时,我只是笑了一笑,不做评论。
碑文原就雕刻好了,有关父亲的碑文一直用宽边的胶带纸蒙着,"卒于某年某月某日"须重新篆刻,相片也需重新置换,我跟雕刻师傅交涉,碑不用重新取出来,辛苦他们现场施工,师傅面露难色,但我最终坚持,亲朋不知晓内幕,都不能理解,妻子在旁边理解了我的心思,也赞同我的决定。
碑依旧向北倾斜,家之南、墓之北,永远朝着家的方向,不曾改变。
(二)回 首
十多年前,我偶尔写一些乏善可陈的句子:"花是倒悬好,人如倒悬何……"大都是有出处的亦步亦趋学步之作,给粗通文墨的父亲看,父亲总会说:"好句!好句!"等到父亲出版他人生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最后一本诗集《稀龄学步》的时候,父亲想让我给他的诗集写几句话,我记得我当时答应得比较爽快,但等到父亲的诗集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迟迟交不出来。
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父亲退而求其次,要我为他的诗集设计封面,这倒是不难。我跑到乡贤著名画家赵溅球先生家中,要他题"稀龄学步"签,赵老师横竖各题了一幅,又画了一幅"极目楚天舒"的画,正好做封面,我挑了一幅自己的花鸟画习作"鱼乐图"做封底,把封面封底的颜色统一了一下,取竖式签放封面的右上角,轻松搞定。
书的颜色是浅浅的草绿色。父亲是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干部,一直向往成为一名身着绿色军装的战士,绿色也代表蓬勃生机,取之成书,深得父亲之心……
是多么遥远的记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诗?为什么写文章?我或许可以用生命的转折来回答。譬如安逸、譬如简单、譬如寂寞、譬如有话要说……
我也是经常这样回复的,可是,又感觉并不尽能。
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我并不想深究。
记得我四十年前读第一本大部头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时候、记得我四十年前读第一本《徐志摩诗集》的时候,就注定了我此生会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时会想,我为什么要写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并没有什么答案。
反复追问,仍然没有答案。
既然如此,何必深究呢。
于是,文章源源不断的写;于是,诗源源不绝的写,我感觉我远没有杨郎才尽之虞,那就顺其自然好了。
我想,我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人,但我也搞评论,那就是说,我必须做到兼收并蓄,还必须做到求同存异。
就文章而言,我不仅喜欢朱自清似的美文、杨溯似的律(规律)文,还喜欢沈从文、巴金一样的平民文字,接触三毛以后,对她的那种以对话巧妙组合成文的方式,愈发喜欢。
当然,喜欢中也应有取舍。
杨溯的散文,单篇都是美文。但读得多了,你会发现他走入了自己设定的模式里,成了公文式的套子里的人,成了万劫不复的循环播放器。
还是更喜欢沈从文、巴金平民化的文字,还是更喜欢小女人似的三毛文字。看似人人都会写,人人都能写,而又匠心独运的文字。
就诗而言,我更喜欢唯美的徐志摩、席慕容、拜伦,但也不排斥那些用身体写作的激进派诗人。
八十年代初看艾青编辑的"中国诗歌大系",那些颇负盛名的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都只有五首诗入选,而艾先生自己有十首入列,就不由在心里冷笑,更看轻这个人,从此不看他的诗。
为什么要如此偏激呢。
年龄渐长,知道了近水楼台的含义;年龄渐长,知道了搂草打兔子的含义,也就释怀了。去年特地在网上买了一本百花版的《艾青诗选》仔细阅读,一个资本家的孩子,也能写出如此大众化、百姓化的诗句,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了。
比时下调侃式的、边缘式的、俚语式的呓语诗,高贵典雅多了。
我非常认同席慕容的一句话:"诗,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席慕容说得斩钉截铁,我信得五体投地。
靠着不断的行走和积累,当然,还有生活的赏赐和厚待,我得以在文字中、在诗行里,找到那个迷失的自己。
这应当是真正让我与文字有交接的根源所在吧。
"书写者回头省视自己一路走来,可能忽然发现,原来走了那么久,现在才开始。"
既然是现在才开始,谈结束尚为时太早。
那就张开双手,扯开双脚,真正的开始吧。
(三)故乡的小塘
离开故乡四十年了,前二十年每年回一次故乡看望叔叔婶婶,后来叔叔一家随儿子迁到株洲、湘潭,回故乡的次数一下降了下来,几年一次,甚至五年才一次,都是承叔叔客住故乡之时回去探视。直到前几年叔叔病故,才坚持在每年细雨绵绵的清明时候,回一趟故乡,祭拜叔叔。
故乡随时都在变化,近几年更甚,有些改变我是能够接受的,但有些改变也是我无法理解的。
不仅仅是清明时节的雨,还有诸多的童年情结,影响了我的心绪,回故乡的心情总是矛盾和忧郁的。我刚决定回一趟故乡,随后便予以否决,我矛盾着、迟疑着,我总怕故乡之行,会勾引起我诸多童年的回忆,而这些童年的回忆,相比现在的故乡,我是愿意忘却的,而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仔细的温习一遍。
我儿时居住的房子,早已经拆了,拆于哪一年,我并没有留意。
今年十一月,婶婶通知我们亲戚朋友回一趟故乡,为她和我两个堂兄的新房贺喜。
原来居住的地方,拔地而起的一套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子外壳已完工,只有内部的装饰亟待解决了。
我从一楼看到三楼,已找不到任何童年残留的蛛丝蚂迹。站在三楼的屋顶上,瞰看前方,原来的菜地里添了不少墓地,老兄少年时代用愚公移山精神开发的山地,已成了他人的宅基地,屋前的一口常年流水潺潺的小塘不见了,成了一条毫无生气的泥巴路,偏右伸展三十度,一口长方形的小塘,成了一片住房。将眼光旋转一百八十度,屋后青青翠翠的两片小毛竹林也不见了,换来的是绵延数里的梯田。两眼聚焦在两片小毛竹林间,令人震惊的是,其间一口清澈见底的小塘也不翼而飞了,心一下沉到谷地,莫名的郁郁寡欢起来。
躲开喧嚣着的人群,我绕到新楼屋后篱笆栅栏边,在大致小塘的位置上逡巡着,踩着亩多见方光溜溜的平地,思绪万千。
过去这里的小塘,曾经是我的皇地,我是塘里的浪里白条,小塘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记忆、快乐、和忧伤。
遥想当年,屋后的小水塘与屋前的小水塘由一条逶迤曲折的小溪串联着,绕屋而过。小溪西起月塘湖水坝,东至兰溪河堤,全程绕全村一周,几十公里,其间支杈溪流星罗棋布,用于全村农田灌溉。
小溪的水常年流淌,夏涌冬瘦。我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在屋边溪涧里举手拦腰设置各种捕鱼器具,捕获各种小鱼小虾。大人是不屑做的,但对我们这些细伢子来说,可是神秘而又快乐的诺亚方舟。
一年总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猫在水塘里,在屋后的小水塘,按着伸进塘里的麻石跳板开始学"狗刨式",无师自通,母亲站在岸边上干着急,后来我用双手按着一个反扣的木水桶,双脚奋力向后蹬,望着围着塘边转圈的母亲咧嘴笑,母亲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篙,气急败坏的用篙尖敲打着水面。塘不大,母亲往东我往西,与母亲捉迷藏,不小心被母亲逮到,母亲总是用篙尖把我拨到岸边水浅的地方,用不了几天,木桶也不要了,可以五、六分钟游一个来回了,母亲事多,见我已学会游泳,最也以无暇顾及我了。
屋后的小水塘,是我们全家和隔壁两户农户的生活用水,也是饮用水,基本上没有放养过鱼,但过去生态很好,溪涧与水塘有一个小月口相连,涧水和塘水是连着的,塘水静止时水清见底,里面小鱼小虾历历在目,时常也有中等个头的青草鲢鱼,在塘中间结队遨游。
小时候,我们用一块正方形沙窗布,用两根小竹杆绑成十字架,十字架四个点连着沙窗布四个角,制成简单的扳鱼筝子,里面丢点在塘边捡拾的敲破了的螺蛳、蚌壳,用一根麻绳一头系着十字架的中心点,一头牵在手里,丢在塘边水里五、六分钟,捞上来即有收获。鱼获种类繁多,以肉嫩子、烧火皮、半皮子为多,家里也能时常制作一碗鱼汤打打牙祭,改善生活。
家家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凌晨五点左右大人们陆续起床,男人起床到水塘里挑水,灌满自家的大水缸。
夏秋两季的水塘,向晚是喧嚣的乐园。忙碌了一天的男人,在塘边洗澡擦身,女人则濯衣、洗发、聊天,嘻嘻哈哈,响彻云宵,我们这些小孩子更兴奋,在水里扑腾、在塘垄上追逐,从塘垄上鱼跃入水,充分展示自己,不甘寂寞。
屋前的小水塘,也很重要。一个偌大的菜园,几十块菜地,灌慨之源泉。人们不用肩挑车推,用一个尿桶,走几步路打水,手提着给菜地浇水。我们杨家的菜地,一面临水,不用桶子,可直接用长木瓢舀水浇菜,水源的丰富、优良的生态,菜园里的时蔬清翠欲滴,供应全家的食用,还有很多的盈余拿到集上出售,供我们小辈换取学杂费。
几十年的时间,故乡已经是物是人非,故人相见已不相识,几口小塘,只留存在我的梦里、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但我仍然执拗的记着小塘,记着伴着小塘所发生的一切。


作者简介:
杨斌:公务员,民主人士,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省直书画家协会会员,书画评论家,书画鉴定家,诗人,专栏作家。2017年在《益阳城市报》开辟整版"杨斌专栏"和"红盾人物"诗栏,著有诗集《秋思》、《时光漫步》等,书画评论集《画说潇湘》。另小说散文刊载于报刊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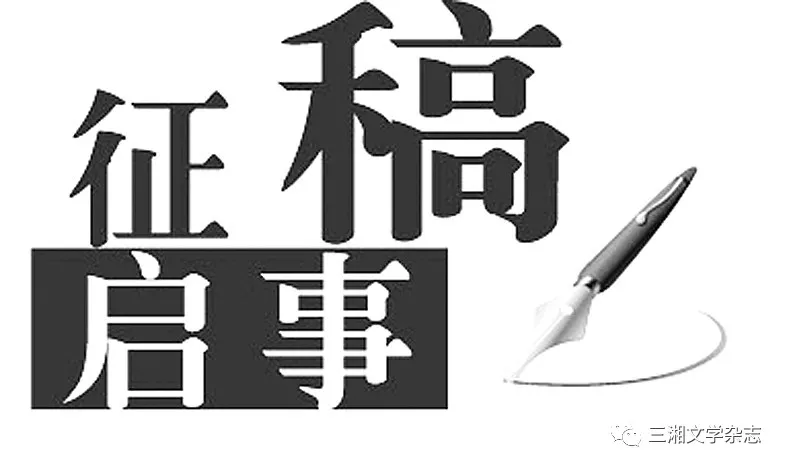

《三湘文学杂志》关于举办首届“三湘文学奖”的通告
为繁荣诗文创作,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培养和扶植文学的新生力量,三湘文学杂志决定举办首届“三湘文学奖”,现将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参赛形式及对象
“三湘文学奖”,以“三湘文化”为主题。三湘四水,物华天宝,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喻;热土潇湘,人杰 地灵、英雄辈出,不负“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盛名。
“三湘四水”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媒体还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都爱用“三湘四水”来代指湖南。不过对“三湘四水”一词也有很多种提法与解释,“三湘四水”中的“四水”一般是指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河流。从三湘文化中发掘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题目自拟。
面向喜欢文学的所有作者,不限年龄,不分民族,不分学历,以文为本。
二、参赛方式
以原创作品首投,一旦发现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现象,即取消参赛资格。
三、联系方式
参赛作品注明通联,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和作者简历,以裸诗(一至五首,总行数不超过三百行)、文章(一至三篇,每篇两千字以下)或电子文档的方式按文体的种类发送至:
散文邮箱:
1130493187@qq.com(雷响玲)
小说邮箱:
389770404@QQcom(周丹)
诗歌邮箱:
2047744654@qq.com(岳小宏)
四、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传奇故事》杂志社
《三湘文学》杂志社
2.媒体支持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报
湖南经济报新媒体中心
3.承办单位
《三湘文学》编辑部
4.评委
李发模,著名诗人,原贵州省作协副主席
王大煜,《传奇故事.校园文学》总编
刘川,《诗潮》主编
文翊,《粮食科技与经济》执行总编
刘占龙:部编版《伴阅读》语文素养教材72本副总编
袁理鹏,部编版《伴阅读》语文素养教材小学分册主编
廖小祥,《邵阳晚报》总编
刘华,《遵义晚报》总编
冬箫,中诗老总,徐志摩诗歌奖评委
梁尔源,湖南作家协会专委,湖南诗歌学会会长
王晓波,中山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山市诗歌学会主席
总策划人,邹中海
执行策划人:释圣静
秘书长:彭振起
五、奖项、奖励办法及其它
一等奖两名
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五名
优秀奖十名
入围奖二十名
1.所有参赛作品都放到三湘文学杂志公众号上展示。
2.获奖作品在三湘文学杂志上或合作的杂志媒体上重点推荐。
3.成为三湘文学或校园文学杂志的签约作家。
4.颁发获奖证书。
5.作品质量、浏览量、点击量等都将作为评奖的辅助依据,举办方有最终解释权。
六、征稿日期
自2020年10月8日至2020年11月8日止。
本次赛事经费,由三湘诗人王建军先生独家赞助。
一一三湘文学奖大赛组委会
2020年10月6日


微刊主编:雷响玲
